打破沉默的螺旋后,哪些人可能加入自由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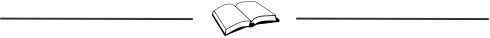
正如将这种文化战争称为“智识战斗”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说:
每个人都肩负着社会的一部分;没有人能被他人免除自己的责任分量。如果社会正在走向毁灭,那么,没有人能为自己找到安全的出路。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必须奋力投入这场智识战斗。没有能够冷眼旁观;每个人的利益都系于这场战斗的结果。无论是否选择加入,每个人都被拖入这场伟大的历史性斗争,这个时代将我们推向这场决定性战斗。(米塞斯1981,第468-469页)
为了恢复资产阶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必须进行这场“智识斗争”。
没有国家的影响,文化将回归古老的自然文化。
然而,由于国家及其对媒体和教育体系的影响,这种情况不会自动发生。
为了扭转国家文化,要求人们付出最伟大的协调一致的努力。
米莱已经理解道这一点。
只要国家存在,自由意志主义者就必须拥抱文化战争,甚至从国家制度内部去拥抱它。
低估文化战争的重要性,不将文化留给它自己(如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将它留给别人,是这两类人犯下的大错。
由于无知和忽视,他们将文化领域留给左派,而没有与之战斗。
许多保守主义者聚焦于他们私人的宗教和生活方式。自由意志主义者则将他们的论证局限于经济领域。
他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及其更高的生活水平足以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存活。
但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已经知道:“永远保持警惕是自由的代价。”
米莱一次又一次强调,一种经济制度也需要道德合法性,从而需要支持该制度的价值观。
如果社会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那么,无论资本主义创造了多少财富,它都无法长期维系。
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政治认同是他们的普遍的文化世界观的产物。
重要的是理念和价值观。
米莱确切地理解这些联系,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他理解文化战争的意义,并表明了如果人们接受文化战争并严肃地从事这场战争,那么可以实现些什么。
因此,米莱不仅谈论经济主体,也讨论文化和道德主体。他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灵魂上的痼疾。
米莱打了这场更好的理念与价值观之战。
他激烈地与左派宣传的观念作斗争。
他毫不畏惧地站起来反对平等主义、结构性受害者理念、平权运动、社会正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无神论、气候癔症、极端女性主义、认同政治学、跨性别主义、2030议程和政治正确。
由于米莱展开了冒犯性的、百无禁忌的斗争,他打破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
“沉默的螺旋”一词是传播学家(communication scientist)伊丽莎白·内勒-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创造的。
沉默的螺旋说的是一种公共舆论动态。
它关乎的是为了避免自己被孤立而能够或必须公开展示的意见或行为。
沉默的螺旋是这样运作的:因为害怕自己被社死和排挤,人们必须对自己的立场缄口不言。
人们认为,(所谓的)少数意见是不被支持的。由于这种立场现在在公众中更没有代表性,(所谓的)多数意见看起来在人群中比实际情况更强大。
这就鼓励了多数意见的代表们。他们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加洪亮。
结果是,更多的少数意见人群开始保持沉默,多数意见的代表变得更大声,如此往复。
这种螺旋一直强化,直至一种意见陷入沉默,而另一种意见主导了公共舆论,尽管被边缘化的意见很可能仍然在人民中广泛传播。
因此,这种沉默的螺旋关乎的是由于害怕孤立而在公共舆论的框架内出现的传播垄断。
人们即使看到社会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也缄口不言。
他们不再去解决问题,因为害怕被孤立。
害怕他们的言辞会伤害他人。
孤立可以仅仅是不再有人向你打招呼,朋友们转身而去,也可以是最极端的情形:一个个体成为社会的弃儿。
米莱的示范提供了一个公共舆论可以如何迅速扭转和沉默螺旋被打破的极佳例证。
米莱从不羞于谈论无政府资本主义和提及奥地利学派。
恰恰相反。在阿根廷,以庇隆主义和基什内尔主义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主导了公共舆论数十年。
在米莱现象及其以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之前,任何不追随左翼风潮的人都被认为是右翼极端分子或纳粹。
由于米莱现象,人们再一次敢于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自豪而开心地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
哈维尔·米莱成为自由意志主义意见的喉舌。
因此,许多人意识到,他们的意见并不孤单。你不必害怕孤立。即使一个国家的总统也在表达这些理念。
人们意识到,许多人都持有自由意志主义观点,人数多于人们的猜测。
突然,据称不关心政治的邻居就跳出来说自己是米莱的粉丝,然后事实证明,他就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接受言论禁令或禁忌。
只有这样,自由意志主义者才不再会被沉默的螺旋所排斥。
他们的意见不再被人们拿着如下座右铭来嘲讽:“没有国家,谁来修路?”米莱把桌子转过来了。
他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政客卑鄙无耻和荒唐可笑。
米莱说政客就是寄生虫。
而这些寄生虫的言行举止看起来仿佛没有他们,阿根廷人就活不下去似的。
但是事情正好相反:
没有被剥削者,政客们就活不下去。
政坛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
他一次又一次强调,政客们是谎言家和窃贼。
如果这些洞见被人们重复和传播,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你做梦都不敢想的变革。
因为有时候,公共舆论只是一个假象,而阿根廷看起来就是这样。
假象可能仍然横行,但背后的价值观已然崩溃。
当假象崩溃时,其背后的巨大空洞就会立刻暴露。
撕开这种假象,需要开路先锋。这些先驱不害怕孤立。
他们不会响应公共舆论。
他们不会像风中的旗帜一样改变自己的思想。
哈维尔·米莱就是这样一种先驱。
多年来,他让自己在脱口秀上疯狂攻击,甚至像一个极端右派分子一样。他受了很多骂名。
正如伊丽莎白·内勒-诺伊曼解释的那样,社会性的局外人是那些开始抵制沉默螺旋的人:先锋派、异教徒、传教士、改革家、科学家和艺术家。
简言之:更被害怕被孤立的人。
因为他们能够克服恐惧,或者有意选择被污名化。
用文学语言说,人们为堂吉诃德这样的人树立了一座丰碑。
“只要我们的羽旗还在毅力与信念之风中飘扬,他们是巨人还是风车无关紧要。”
无论巨人还是风车,无惧总是重要的。
闻鸡起舞、挺身而战总是重要的。
为真理和自由而战。
成果是其次的。成果会有的。
堂吉诃德是否被孤立无关紧要。
他是一个英雄。毋庸置疑。
正是这些堂吉诃德,这些被压制的少数,不再保持沉默。
他们心中的硬核观念,随时可能脱口而出。
然后,根据内勒-诺伊曼的意见,这些少数派有两个结果。
要么作为一个秘密教派退出社会,要么获得年轻人,前卫的人的支持。
米莱正是如此。米莱在年轻人中尤为受欢迎。
在阿根廷和其他地方,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越来越时尚,就像过去成为左翼和崇拜切·格瓦拉很时髦。
米莱桀骜不驯。
他站出来反对建制派,反对特权阶层。
他的答案是资本主义。米莱已经做到了: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可以被公开代表,而不会有被孤立的奉献。
无政府资本主义已经被社会接受。
归根到底,他打破了国家主义解释框架的霸权并埋葬了它。
米莱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自己在政治上收割了他的文化战争的成果。
文化战争与政治的联系如下:政客通常会响应公共舆论。
他们试图代表公共舆论。
反过来,文化战争塑造了公共舆论。
任何仅仅是从政的人都会成为公共舆论的奴隶。
毛里西奥·马克里就是这样失败的。
马克里不敢进行任何重大改革,因为公共舆论不允许。
渐进的改革失败了。
另一方面,那些仅仅参与文化战争的人面临这样的问题:政客在竞选期间以民意为导向,例如,为了当选而谈论自由理念,但是,当他们当权时,他们就会实行完全不同的纲领。
由此可见,除了文化战争,你必须成为政治活跃分子,以便让正确的人当选和正确的理念被实施。
因此,米莱是独一无二的。
他不仅通过他的自由理念启蒙和传播播下了种子,而且在政治上收割了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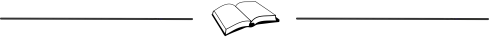
文化战争很现实。一切都岌岌可危。
西方世界的自由受到了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左翼绿色分子的广泛威胁。
而他们貌似正在取胜的轨道上。
为了防止这种巨大的危险,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必须锻造一个联盟。
因为正如米莱所解释的那样,政治与市场相反,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如果我们没有当权,他们就会当权。
如果左派当权更久,自由的西方文明就会倒退。
反左联盟包括非觉醒自由意志主义者、灵活的保守主义者、非国家主义的传统主义者和爱国者。
他们的关切是相容的和互补的。
他们的共同敌人是社会主义。
鉴于社会主义给西方文明造成的危险,这些群体应该暂时搁置分歧。
共性应该摆在前面。
阿根廷思想家和米莱的朋友奥古斯汀·拉赫是这种联盟的公开倡导者。
他说到了在文化战争中联合这些群体的“新右派”。
总之,“新右派”联盟构成了政治建制的根本对立面。
正如左派是一个集体名词一样,右派也可能是这样。
毛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绿党分子、觉醒主义者不会觉得将自己归类为左翼有什么问题。
右派不是如此。
“右派”由保守主义者、爱国者、传统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主义者、米塞斯主义者、罗斯巴德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等等构成,它们是碎片化的,常常彼此争斗,这对于左派的政治辩论不利。
“右”和“左”这样的术语简化了现实的复杂性。选民更容易理解现实了。
人民不需要了解毛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或者哈耶克主义者和罗斯巴德主义者之间的区别。
他们只是左派或者右派。复杂性的减少使之更容易理解。
如果“新右派”群体因为认为“右派”一词是邪恶的,从而放弃这种简化,反社会主义方阵就会解体,抵制左派会更加困难。
但是,“新右派”怎么才能彼此互不呢?这个联盟真的是相容的吗?
自由意志主义者希望削减国家的规模。
文化保守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承认诸如婚姻和家庭之类的制度的重要性——这些制度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但是可能被非常迅速地摧毁。
因此,他们敦促人们警惕左派的建构理性主义。
爱国者希望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诸如2030议程之类的全球主义计划和非民主精英推动的平等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爱国者是彼此互补的。
“新右派”将抵制左派风潮的人团结在一起:
对教化灌输失望的学生;
在学校再也不能学到任何东西和得不到令人不悦的问题的答案的孩子;
关心孩子教育,不喜欢性早熟和希望孩子在学校学点有意义的东西的父母;
厌倦了总是被当成坏人,反对“有害的大男子气概(zeitgeist)”这个说法的男人;
反女性主义、憎恨妇女法律特权和配额制,以及抗议性别仇恨的女人;
不感到愧疚的异性恋;
厌恶被觉醒意识形态政治工具化的同性恋;
担心无限制的大规模移民和激进伊斯兰主义传播的本地人;
努力工作和融合,但是被怀疑是为进入福利国家而移民的移民;
接地气的,厌恶全球化公司觉醒主义的工人。
这个联盟反对左翼纲领:进入福利体系的移民,过多的福利国家,性别语言,气候癔症,政治全球化,反基督教化,政治正确和家庭的国家化。
新右派捍卫宗教自由、教育自由、传统家庭、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它承认基督教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观。
共同的观点是,在一切领域,自由都是最好的。
这个联盟也有分工。
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好承担解释何种社会更有生产力和更公正的工作。
保守主义者可以用关于文化、精神和道德的论据来补充这些理念。
例如,保守主义者可以表明,跨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导致庞大国家发展起来的,家庭价值观是如何被破坏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如何被削弱的。
而爱国主义者反对中心化和全球主义。
米莱支持这种联盟的想法。
例如,他出席了“新右派”理念背后的人物奥古斯汀·拉赫的《文化战争》一书的评介会。
保守主义思想家尼古拉斯·马克斯(Nicolás Márquez)也出席了,马奎斯与马塞洛·杜克洛(Marcelo Duclos)一道出版了一本关于米莱的书,大受欢迎。
米莱称拉赫和马克斯是朋友。
根据米莱自己的说法,他愿意与其他党派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结盟,与右翼分子结盟,与中右政客、保守主义者、共和派庇隆主义者、梅内姆主义者(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和变革联盟“鹰派”结盟(米莱2022,第292页)。
米莱一次又一次朝保守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走去。
米莱不仅让保守主义者、福克兰战争[译注:即英阿马岛战争]中走出来的军人之女维多利亚·比利亚鲁埃尔成为副总统,而且在选举中获得了天主教自由意志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进一步支持。
在其就任之初,他采取了几个象征性的行动,它们完全符合这样一种反觉醒联盟的精神。
例如,米莱禁止他这一任政府使用性别语言,并关闭了INADI中心(西班牙语:Instituto contra la Discriminación, la Xenofobia y el Racismo,反歧视、反排外和反种族主义中心),该中心完全服务于为左翼活动家提供报酬丰厚的职位,并在社会中制造人为的冲突。
202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在妹妹卡琳娜·米莱的倡议下,米莱将阿根廷总统官邸卡萨·罗萨达的“妇女大厅”改成“国家英雄大厅”。
顺便说一句,他的政府中,女性比例是45%,远高于之前的政府。
3月24日是阿根廷的全国真理与正义纪念日(Día Nacional de la Memoria por la Verdad y la Justicia),米莱纪念了左翼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并对军事独裁时期的“30000名受害者”这一神秘数字进行了符合实际的纠正。
2024年4月2日,米莱纪念了死于马岛战争的阿根廷战士,这是一件之前总统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些象征性的行动,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首要关切的事情。
然而,它们获得了所有参与“新右派”文化战争的保守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支持。
在国际上,米莱与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唐纳德·特朗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政治人物已经认识到谁才是敌人(敌人即社会主义)。
米莱的目标是将保守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所有那些反对左翼觉醒日程的人拉到自由这一边。
为了这个目的,2024年2月,米莱出席了CAPC(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美国最著名的保守主义论坛。
他热情地与特朗普打招呼。
然而,米莱的演讲并没有赞扬的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相反,米莱在CPAC上作了一场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优势的经济学讲座。
他谴责堕胎并怒骂后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也采取了清晰的反对左翼民粹主义的立场,并强调了自由贸易的优势。
特朗普在他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种保护主义政策。
保守主义听众为米莱欢呼,包括他歌颂自由贸易的时候。
向“新右派”提供经济学教育,引导他们在一切政治领域都走向自由理念,正是米莱的战略。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