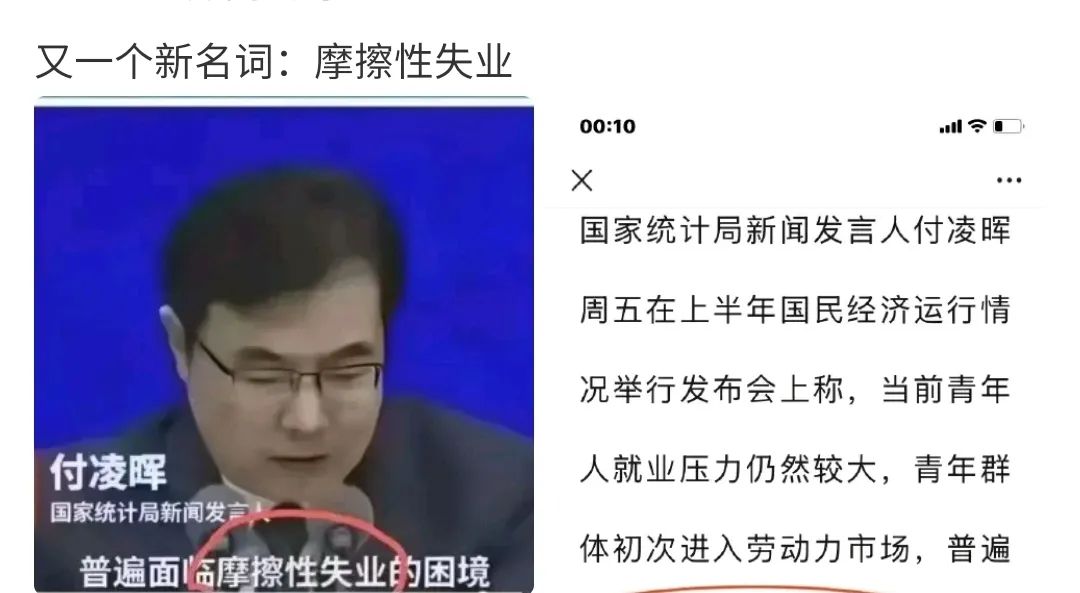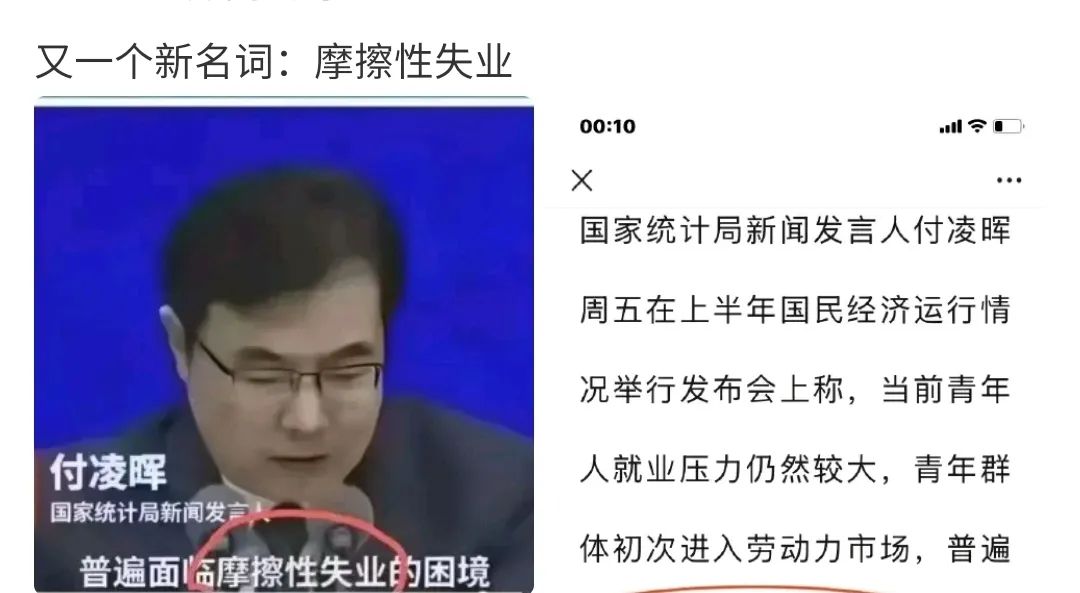摩擦性失业,倒不是什么新名词,而是一个物理学词语用于人的行动领域的错误名词。它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中一种短期、自愿的失业类型,主要源于劳动者与岗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匹配过程中的时间差。失业分为两种,一种是交换性失业,一种是制度性失业。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动的。在一个被干预的市场上,管制当局打着关爱劳动者的名义,出台各种“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措施。比如最典型的,最低工资法,就是将工资率设定在自由市场决定的工资率之上。这时候刺激劳动供给而减少了劳动需求,打破了供求均衡,劳动力市场就无法实现出清。企业将只会雇佣那些能够创造较高边际价值的劳动者,那些无法创造最低工资所对应的边际价值产品的劳动者,将被解雇或者自始至终得不到雇佣。在经济学分析中,我们一定要摒弃集体主义的词汇,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所谓“保护劳动者”,必须多问一句:“劳动者”是一个整体吗,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吗?那么保护劳动者,保护的是哪一类、哪一群劳动者?只要你这样思考了,问题就变得明了。最低工资法保护的,显然不是全体劳动者,而是劳动者中的较高边际生产力的群体,那些较低边际生产力的低技能群体,则受到了伤害。所以,最低工资法往往成为排除低技能劳动者、要求较低工资率的劳动者竞争的手段。例如淘金热期间,华人也大量涌入加州,他们立足未稳,勤奋勇敢,只要有一份工作能够糊口,就愿意以较低工资率就业。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处境的改善。然而这时候,他们就“抢”走了那些懒惰而工资高的美国人的工作岗位。这些美国人于是就撺掇当地的管制当局出台了最低工资法,将华人排挤出局。于是,华人就只能去开洗衣店和杂货铺。再比如19世纪的加拿大伐木业,日本伐木工人纪律严明、工作效率高、要求的工资率低,于是加拿大当局如法炮制,出台最低工资法,将日本工人排挤出局,由此开启了日本人向加拿大内陆地区的迁徙过程。托马斯·索维尔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美国劳工部工作,他凭借直觉和经验数据,告诉他的同僚:最低工资法无法无法让工人待遇变好,反而会导致失业。他的劳工部同事耸耸肩,看着这个傻白甜新同事,两手一摊:谁不知道呢?但是如果不这样干,要我们劳工部干什么!行政部门总是这样,总要干预市场,否则他们的权力如何扩张、如何寻租呢?他们的预算如何增长呢?权力的逻辑就是这样。最低工资法有很多变种,或者说,有些干预政策起到了和最低工资法一样的效果。比方说,最高法院规定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这时候实际上就是变相地规定了最低工资。因为企业核算的时候,当然不是看劳动者到手的工资到底是多少,而是看它为雇佣这位劳动者一共支付了多少成本。因此,强制的高额社保,将大幅度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雇佣成本,实际上就是逼着中小企业减少雇佣、躺平比烂和亏损破产,由此导致更多劳动者失业,以及,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降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那这个时候,交社保的人就更少了,也更加交不起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就会扭曲,会在管制之外寻找新的合作方式,例如劳动者都变成个体户,跟企业签订的不是雇佣合同,而是合作生产的合同,这就不用交社保了。市场总是会寻找突破管制的办法。由此,强制的社保,可能导致社保的进一步崩盘。再比如,规定女职工超长产假,但是休假期间必须工资照发,这实际上也是在规定最低工资,也就是,工作半年,必须拿一年的工资。现在又在鼓励生育,一年发3600的奶粉钱,幼儿园还免费,那么企业就怕的要死,你要是跟下崽一样连着生三个,那就一两年不用工作而拿工资,哪个中小企业能受得了?那么,企业就开始“歧视”女职工了:你到底能不能在半年之内创造一年的价值?或者,从长远看,我损失这半年的工资之支出,能不能在未来通过你的生产力赚回来?鉴于这极其地不确定,未来市场的不确定,你能力的不确定,白拿完这些收入后还可能离职了,那我必须从严审查你的能力、你生娃了没有、生了几个了?因为要是把这些事情不掰扯清楚了,那简直就不是雇佣员工,而是请回来了一个少奶奶。如果这时候又继续叠加干预,不准问婚姻和生育状况,那企业就更加“歧视”了:咱啥也不问,啥也不敢说,但是只要你是个女的,我就不雇佣了,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一切制度性歧视,都是干预主义制造的,然后甩锅给企业。鼓吹保护女职工的人,会将女人从职场上赶回厨房,让她们失去来之不易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重新成为男性的附庸。我怀疑,鼓吹和出台这些政策的人,可能跟女同胞们有仇吧,或者是男权保守主义分子。我们知道,自由市场上,总有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失业总是自愿的。通俗说,只要你愿意屈尊、愿意降低工资率,那就有就业岗位。所以自由市场上的失业,总是劳动者根据自身的处境,主动、自愿做出的边际选择,这就是“交换性失业”。大学生难找工作,在统计局发言人看来,是摩擦性失业:信息不对称,找不到匹配的岗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工作。但这当然是交换性失业,自愿失业。总是因为他们“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找不到工作的。如果他们不是整天眼高手低,把自己看做天之骄子;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价值几何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市场消费者的评值,由此愿意降低期望值,要求较低的工资率,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呢?去刷盘子啊,一个月两三千,再不行就1500,或者去工地搬砖,一定会有工作的。那么,大学生之所以可以承受摩擦性失业,就是在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工资率的工作。这个等待要耗费时间,耗费储蓄。他们之所以等得起,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为其积累了足够的储蓄,可以承受这种不生产而只消费的生活,而暂时不至于储蓄耗尽。假如储蓄耗尽无法啃老就要饿死了,他当然会以最快的速度、以任何能活下来的工资率就业。人,必须工作,才能活下去。这不是任何制度的错。那些由此抱怨市场经济的人完全搞错了,没有任何制度能让人享受不生产而消费、无限休闲的“权利”,这是人类生存不可避免的外在条件决定的,是无法回避的自然事实,因为我们受到稀缺性的制约。假如奢望没有任何找工作、赚工资养活自己的压力,那就只有一个替代选项:由一个中央计划当局给每个人指派职业和工作。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一切自由烟消云散,每个人都变成在锁链和皮鞭下工作、并乞求人家投喂的奴隶。还有一种常见的摩擦性失业,发生在商业周期的萧条期。由于前期扩大信贷投放,人为压低利率,导致虚假繁荣。当泡沫破裂,信贷收缩、利率回归市场,过去错误的投资遭到清算,生产结构发生剧烈调整而缩短,于是,那些过去在错误延长的生产结构中就业的劳动者,发生了失业。当出现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变,因此市场上的生产结构缩短时,会出现工人被抛出较高的生产阶段的暂时性失业,并将持续到他们能够被生产过程的较后阶段重新吸纳为止。
那些过去在高阶生产阶段就业的劳动者,萧条期要想找到一个新的工作,需要大幅降低工资率,需要转换工种,例如从过去的一个白领,转变为蓝领,本身就需要训练,同时还要过心理落差这一关,于是发生了时间上的就业延迟现象。但是把它说成是非自愿的、摩擦性的,就完全是混淆概念。他们当然也是自愿失业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立即做出调整,屈尊纡贵地、要求较低工资率地立即就业,只要他们愿意这样做,如前所述,当然可以很快就业。同样,他们之所以能等得起,是因为有前期的储蓄供其消耗。所以他们是在等待更好的被雇佣的机会,主动选择有利的时机。这必然是他们自愿做出的选择。把这种市场生产结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失业现象,称之为摩擦性失业,是混淆了因果关系。主流经济学认为,这是经济调整导致的延缓结果,因此必须要干预;然而事实上,这种等待过程,恰恰是拖慢了整个经济调整过程的一个因素。须知劳动者并不是像物理学家想象的那样,像机器一样自动运转,没有自由意志,没有选择,被动做出反应。他们总是主动地选择。因此,这种失业是投机性的,而不是摩擦性的。它再次证明,使用物理学词语来形容人的行动,是极其不妥当的,将混淆事情的本质,并导向错误的结果。比喻,绝对不能代替严密的逻辑推理。这就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在经济萧条期,一定要允许工资率和各种价格随行就市,自由地下降,只有这样,才能让劳动者尽快地找到工作,让各种“失业”的资本品重新被纳入生产过程,启动经济复苏的进程。如果这个时候又打着关爱劳动者的名义,不允许价格和工资率下降,那么经济的调整过程就被人为延迟,不断地延长萧条,制造大规模制度性失业。这正是美国大萧条的历史教训。总是不吸取教训,不学好样光学坏样,“为劳动者操碎了心”,在萧条期不断叠加干预,那就等着大规模失业、工资率降低、生活水平下降,经济不断陷入泥潭之中吧。经济学价值中立,只告诉人们因果关系,怎么选择,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如果劳动者非要选择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干预,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后果必定如经济学描述的那样,自己承担即可。你的认知,总是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