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绝对不是新保守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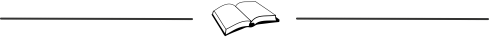
虽然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以赞赏的目光看待米莱踏入政坛和作为总统采取的举措,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
例如,奥斯卡·格劳(Oscar Grau)写了一些分析米莱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文章。
关于前者,格劳认为米莱的方法是干预主义的,在坚持自由与自由市场的修辞的名义下挤压私营部门。
关于后者,格劳总结道,阿根廷总统只是另一个新保守主义建制派政客。
综上,格劳总结道,米莱是一个“骗子”、“国家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并指控其追随者正走在背叛自由意志主义的机会主义道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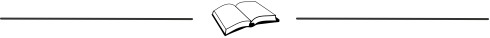
我虽然同意格劳的一些洞见,但他的批评没有考虑许多基本问题。因此他的结论——自由意志主义者应该从智识上和私人关系上与米莱断绝联系——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必须记住四个问题:米莱当权之前的局势如何?阿根廷的替代选项是什么?迄今为止他实现了什么?其纲领之目标何在?
要理解米莱的操作所受约束的背景,情境化至关重要。
约束和机会都一样与特定情境相关,情境设定了边界,在这些边界内,行动者形成了他关于边际收益与其他行动路线之成本的预期和判断。
此外,人们无法避免孟德斯鸠所谓的“推论史学(conjectural history)”,并因而运用解释性理解(韦伯称之为“了解[Verstehen]”)来探讨“米莱现象”及其在正确的方向上启发和激励阿根廷国民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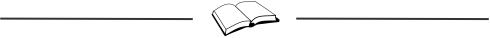
格劳首先低估的是米莱一旦掌权所面临的局势与困难。
除了关于比索通胀趋势的寥寥几句评论之外,格劳很少注意到自从终结政党轮替(the end of convertibility)以来(1992-2001)阿根廷所推行的灾难性政策。
这些政策开始于内斯托·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2003-2007),然后是克里斯蒂纳·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2007-2015),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2015-2019),尤其是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2019-2023)。
这种二十一世纪的阿根廷风社会主义灾难反映在米莱入主卡萨·罗萨达(Casa Rosada)[译注:阿根廷总统府名称]时面临的财政与货币失衡方面。
公共债务总计超过4000亿美元,价值近600亿美元的商业债务即将到期,阿根廷政府濒临违约,自1816年独立以来第十次违约。
此时,阿根廷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记录的美元储备是负数。
造成这些失衡的责任在于过去在任的政治阶层。
关于美元短缺,过去的决定是以相对于外汇和和大宗商品的高估汇率锁死比索,这就造成了所有价格管制的典型效应。
随着人们争相弃用比索,造成了美元挤兑、外汇短缺和收支赤字,这抽干了国内生产。
基什内尔主义者不允许通过让汇率调整到市场出清水平,限制公共支出和限制开动印钞机来解决问题,而是以资本和汇率管制的形式进行进一步货币干预来对抗这些趋势。
出口商被迫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放弃他们的美元收益,他们被征掠了。
同时,特权进口商得到了补贴,国家向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开放的通道受到了限制。
米莱上台时,阿根廷有18种不同的美元汇率。
这种景象招致了政治裙带主义,恶化了汇率风险,并且扩散了经济计算的混乱。
这些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不可维系的政府支出水平。
受艾薇塔·庇隆[译注:阿根廷著名政治人物庇隆夫人]的名言“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诞生权利”的推动,社会计划成倍增加,公共部门的范围急剧扩大。
压迫性的税负水平、繁苛的劳工立法、错综复杂的商业限制很快接踵而至。
财富开始实际上被私有化,但仅仅归于一小群选民,他们没有参与劳动分工,专事秘密支用他人资源而未予补偿。
财富私有化的另一面是痛苦在社会上扩散了。
到2023年11月,贫困率升至55%,而赤贫水平达到了17.5%。


由于没有能力在不损失税入的情况下通过进一步征税压榨私营部门,也无法在国际信贷市场上处置债务,阿根廷央行开始将财政赤字货币化。
自2002年起,阿根廷政客利用通货膨胀作为超出法定税收的公共消耗和挥霍的融资手段,他们将成本外部化,转嫁给(货币)储蓄者、债权人和固定收入者及低收入工薪族。
最重要的是,国家精英们还进一步释放比索,为所谓的准财政赤字提供资金,对应的做法是为了将部分超额比索“存放”在央行,而向商业银行支付日息和月息。
由于实际年化利率随着物价上涨的几何趋势而上升,到 2023 年 11 月达到253%,这些付款构成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10%的内生货币创造来源。
最初作为限制货币供应量的措施变成了通胀失控的最棘手来源之一。
从 2011 年到 2023 年,包括央行无偿负债和有偿负债在内的大规模基础货币增长了116 倍,其中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上一任总统任期内。
在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执政的四年中,央行所扩张的基础货币数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2%,其中仅在最后一年就增加了13%。
当米莱入主政府时,阿根廷深陷经济、货币与财政危机。
长达十多年的长期宽松货币与财政政策之恶果立刻全盘扑面而来:通胀率达到每天1%,年化通胀率3700%,同时财政赤字占15%GDP(财政部5%,央行10%),以及长达12年的萧条。
鉴于过去二十年阿根廷一直处于制度性混乱状态中,米莱发现,他面前很多条路都走不通。


作为阿根廷总统,米莱明白,不管其学术履历如何,此时他已经成了一名政客。
而作为一名政客,还是自由意志主义政客,必须考虑特定的时空情势,如果他想成功维持和扩大选民的支持的话。
在绝不转入错误方向的情况下,自由意志主义政客有时候必须妥协。
根据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的意见,自由意志主义政客必须采用双重策略。
他应该研究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原则,并教导一般公众领会这些原则及其应用,从事传播自由意志主义观念的工作。
这方面无任何妥协可言。
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长期目标,自由意志主义政客也应该寻求迈向理想,但不违背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的可能过渡计划。
如果不可能规避短期的妥协,那么,只要方向正确,他可以作出这种妥协。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采取远离更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一整套措施。
政客和官僚机构(或深层政府)带来的限制,一般公众是不了解的。
自由意志主义政客必须利用其特定时空的知识,评估现实政治生活所提供的实际限制,并认识到在任何历史时刻,条件所允许的理想之最大可能。
只有采用这种双重策略,人们才能避免穆瑞·罗斯巴德所认为的有害于推进自由的两个极端:“右翼机会主义”和“左翼宗派主义”。
如果说前者是“没有原则的政治操作”,无法为政治行动提供明确的根基(non-arbitrary foundation),那么后者就是“没有政治考量的原则”,会阻碍实现最佳可能之善的具体目标。


尽管格劳将他描绘成一个平平无奇(plain)的新古典主义者,但米莱深研过自由意志主义和奥地利学派观念。
除了2014年阅读了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第10章之后“皈依”奥派之外,米莱还阅读过《人的行动》三遍,并熟悉哈耶克、黑兹利特、柯兹纳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
虽然米莱仍然有某些货币主义的残余,但是称呼他是一个数理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至少也是不准确的。
没有哪个货币主义者曾经像米莱一直所做的那样,赞成废除央行,货币非国家化和紧缩价格。
此外,他还写了好些书批评新古典学派/芝加哥学派关于垄断、市场失败和反托拉斯的观点。
还有,只要有可能,他就传播这些观念。
不仅诉诸“人民VS精英”这种修辞,还不断启蒙公众认同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之道德、经济甚至审美优越性,这使得米莱得到近56%的选民支持。
聊举一例,2021年,在赢得春季初选后不久,米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启动了六堂奥地利经济学派系列公开课,其中最后一课复刻了亨利·黑兹利特的“一课经济学”。
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罗马(梅地亚赛特电视台时政节目“Quarta Repubblica”)、马德里(“Vox-Viva24”节目)上的著名公开演讲和采访证明了他上台后一直在持续向大众传播这些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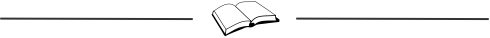
关于双重战略的第二部分,可以应用类似的理由。
在选举期间,米莱的竞选政纲是紧缩政策,承诺削减公共部门的支出和普遍减少税收与管制。
然而,他首先要做的是终结通胀,他最新的著作详细讨论了这一主题,此书取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书名(“通货膨胀的终结[El fin de la Inflacion]”)。
他设想的美元化计划不是要求阿根廷加入美联储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希望让印钞机远离阿根廷特权阶级(the Argentinian caste)的视线,让生产阶层能够以他们明确偏爱的货币单位进行自由交易、储蓄、计划和计算,从稳定性和独立性考虑。
只是这种货币单位恰好是美元。
为了实现这些成果,米莱想出了一个分阶段的过渡计划,但大体上信守了他的许诺。
米莱知道,自己没有议会多数票来进行结构性改革,因此避免恶性通胀危机和又一次违约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用今天的眼光看,米莱十分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米莱11月份接手,当时批发价格月增长率是25.5%,而今年7月最新月通胀率是4%。
根据格劳的意见,通胀的降低,是通过混合了一系列致力于禁止人民挤兑美元,哄抬美元价格的国家主义手法实现的。
好吧,价格和汇率管制显然无法辩护的。
尽管如此,这些管制在米莱掌权时已经存在了,因此它们不可能是重要的肇因。格劳忽视了价格上涨被遏制,是两个相互交织的现象造成的:货币释放渠道缓慢但稳步削减,货币制度质量提升。
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制度质量的变化会改变货币质量、对货币的需求,进而改变货币购买力。
事实上,米莱在执政的第一个月内就实现了财政盈余,并宣布消除财政赤字没有商量余地,从而大大改善了阿根廷的货币制度。
通过这种方式,他建立了稳固的货币锚。
由于不再需要通过印钞来为无休止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通货膨胀预期也随之降低。
最近,政府宣布不再允许货币基础增长(“emisión cero”),进一步提高了货币制度的质量。
正如罗斯巴德深刻指出的那样,决定法定本位制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公众对“发行当局可行性”的信心。
由于法定货币是由政府间接发行的,国家偿付能力就成为货币价格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考虑到国家偿付能力是通过将未来的基本财政盈余折现到现在来评估的,米莱的紧缩措施不仅锚定了未来的货币供应量,而且迅速刺激了货币需求。
同样,通过重组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货币制度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有息负债(Remunerated liabilities)被取消,基础货币大部分由外汇储备支持,外汇储备从负105.45亿美元增至274.39亿美元。
虽然格劳的意见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些措施,但这些措施对降低通胀和降低利率起到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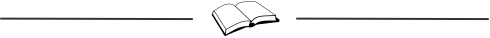
人们可以正确地主张,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应该乐观地看待政府违约。
从托马斯·杰斐逊到穆瑞·罗斯巴德,出于规范理由或实证理由,正统的自由意志主义关于公共财政的立场都是非常明确的:否定公共债务。
然而,话虽如此,人们也应该考虑政府违约的政治成本,这种成本可能非常严酷,尤其是在一个像阿根廷这样如此频繁地违约却从未实现真正复苏的国家。
考虑到这些政治成本,米莱决定推进消除赤字开支和积累预算盈余的计划。
遵从罗斯巴德的意见,政府有三种方式可以重整账目:增税、降低政府支出和私有化国有资产,或三者并行。
而第一种方式是有害的和不正当的,第二和第三种是健康的和完全正当的途径。
那么,在这方面,虽然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正确批评米莱政府对特定税种(进口团结税[impuesto pais]、燃油税和工资税)的增税,但预算盈余的更大部分是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按真实价值计算减少了几乎35%)实现的。
米莱政府已经在阿根廷创造了一项新记录,在其任期的前7个月,解雇了最大数量的公务员。
根据阿根廷财政分析研究所(Instituto Argentino de Analisis Fiscal)公布的公共职员最新报告,在米莱任职的前半年里,30936名政府雇员被解雇。
米莱另一个从一开始就作出重大推进的重要领域是去除管制。
从他的《紧急状态法(Decreto de Necesidady Urgencia)》开始,从租金管制到法币法律,米莱取消了300多项管制,这些管制自独裁者翁加尼亚(Ongania)时代(1966-1970)就一直在扼杀商业。
格劳忽略了以下事实:这种取消管制的法令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修改《民商法》第958条,据此,政府将法律规范降级为合同意志的下位计划(译注:即法律不得凌驾于自愿合同之上)。
既然通胀和管制是一种税收——因为它们都使政府能够实现对社会资源利用的实质性控制——那么米莱的上述成就大大减轻了整体财政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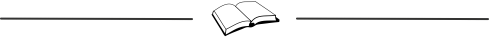
现在,随着他的改革计划(《基础改革法案[Lay Bases]》)最终被国会两院接受,某些私有化将浮出水面。
这将增加预算盈余中可归因于合理和节约的财政紧缩方式的部分。[译注:私有化国有资产将减少总财政支出,并直接增加当期财政收入。]
此外,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放松管制,同时加大减税力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进程已经开始。
2024年8月初,政府颁布了第697/2024号法令,取消了所有与牛有关的牛肉切割税和猪肉出口预扣税。
与此同时,该法令还规定将所有动物蛋白的预扣税降低25%,并永久性取消乳制品的出口关税,估计共有1.3亿美元将返还给生产者。
与此同时,米莱政府取消了预扣增值税和商业销售利润。
此外,米莱还将团结税(impuesto pais)降至 7.5%,并宣布到2024年12月将取消进口税,这大大缓解了商业和企业压力。
现在,人们可以说自由化的速度还不够快,但不能否认其方向是正确的。
是的,米莱不得不做出妥协,尤其是因为他在议会中并不占多数。
自由前进党(米莱的政党)在众议院只占15%的席位,在参议院只占10%的席位。
此外,他的大多数党员只是政治盟友,对奥地利经济学和自由主义并不了解。
然而,米莱的目标是明确的,并在7月总统与各州州长签署的《五月公约》中得到了确认。
该条约的十项基本原则包括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将公共开支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以及实施 “减轻税负、简化阿根廷人的生活和促进贸易”的改革等。


格劳对外交政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米莱在“国际政治 ”中的定位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阿根廷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一层面施加任何影响。
米莱对国际阵营的支持和变化并不意味着他的理想与之前有何不同。
实际上,他的外交政策立场纯粹是一封自荐书。
此外,许多南美国家的现实选项--这也是公民的看法--要么与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欧盟国家)在一起,要么是与社会主义者及其 “朋友”(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在一起。
最近,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在普京、某某某和阿亚图拉(the Ayatollahs)[译注:阿亚图拉,伊斯兰什叶派教徒]的支持下,以欺诈手段再次当选,这就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由于近二十年基什内尔主义者与这个 “东方”阵营的不断调情,以及明显的腐败和管理不善(例如,想想科维德时期费尔南德斯想要的 “莫斯科行动”(Operación Moscú),该行动允许在阿根廷大规模分发“卫星五号”疫苗[译注:俄罗斯产疫苗]),米莱作为其反应的一部分,可能会将目光投向光谱的另一侧,这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人们可能如何看待阿根廷在国际事务上的合纵连横,在“新保(neocon)”一词的传统意义上,米莱都不是“新保守主义者”。
没有哪个新保守主义者像米莱那样明确地(或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持续)表示,国家/政府(state)(包括以色列和乌克兰国家/政府)是一群恶棍组成的,并表示深深地“憎恨”国家/政府。
没有哪个新保守主义者这样做过。
此外,新保守主义者捍卫对外干预,作为对福利-战争国家(welfare-warfare state)的普遍支持之一部分。
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不仅是一个反苏的军国主义者,而且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支持者。
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拥护会逐渐滴灌(instill)公民自我牺牲和高尚举止的“保守的福利国家”。
相反,米莱是国家干预、反歧视政策、家长制和福利国家的激烈批评者。
他属于一个另一个同盟。
像从孟德斯鸠到巴斯夏,从科布登(Cobden)到米塞斯那样的传统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那样,米莱将自由市场看作更和平的国际关系的载体,将放弃自由市场看作战争的前提。
米莱从事着普及激烈反对国家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奥派-自由意志主义观念。
例如,从“穆瑞·罗斯巴德”到“伟大的汉斯-赫尔曼·霍普”,他不断地援引和鼓励人们阅读自由意志主义作家的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格劳谴责米莱是新保守主义者,同时批评他支持特朗普和正在成为特朗普的盟友(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一直是过去二十年来所有美国总统中干预主义色彩最淡的一个),是非常讽刺的。
最后,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米莱的地缘政治立场和亲北约立场,就热切地宣布米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么他会如何评论米塞斯呢?
米塞斯在看待战后欧洲问题时认为,为了避免永久地全面屈服于极权主义,要支持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建立“永久而持续的联盟”,支持“将所有权力授予一个新的超国家权威/政府”。
人们可能说,米塞斯的评论是在特定历史时刻作出的,仅仅适用于那些条件下。这听起来是合理的。
但是,那么,为什么米莱的立场和声明就要受到不一样的待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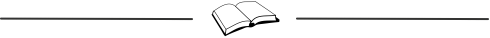
自由意志主义要求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
人们应该从智识上和私人关系切断与某人的联系,仅仅因为他可能没有贯彻完全的自由意志主义理想,这种看法不仅在常识上是古怪的,而且被穆瑞·罗斯巴德本人拒绝了,他不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方针,罗斯巴德在1990年代将这种态度类比为“正统兰德主义者的灾难性疯狂之路”。
虽然人们可能期望、渴望和请求米莱做得更多和更快些,虽然人们可能批评他的这样或那样的妥协,但人们不可能看不到他正在使阿根廷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迈入政坛已经意味着自由意志主义观念的传播和贯彻的一种范式变化。
正如赫苏斯·胡尔塔·德索托提到的那样,感谢米莱及其政治成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阿根廷与拉美城市中,常常能够见到人们夹着《人的行动》走在大街上。
DC Consultores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阿根廷人相信庇隆主义与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一起完蛋了,一个有米莱的新时代开始了。
那么,米莱带来的范式转变不仅仅是一种修辞,而且是一种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希望的历史性的现实。
只有观念,而不是其他途径才能改变世界。
自由万岁!
2024年9月17日
米塞斯学院官方网站


往期推荐

对不起,你不赞成私有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