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管阿姨不开门,是什么给她的底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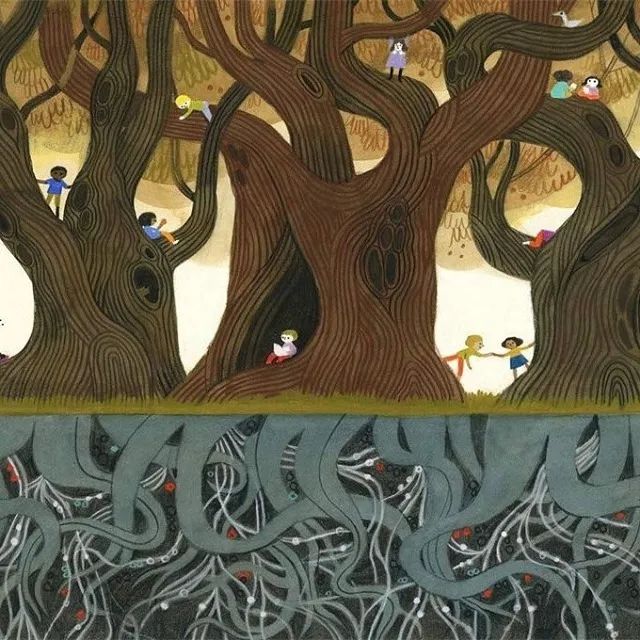
from bigbigwork
一
当你需要一个人帮你办事,一定要清楚他是对谁负责的。说白了,就是他的利益在谁手里。利益在哪,他的行动大概率就会在哪。
如果你是直接付他钱的,你是他的老板或者客户(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东西),那简单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如果你是一名公办学校的大学生,你想凌晨出门赶飞机去见亲人最后一面,你对面的宿管阿姨是对谁负责的,这个问题就很关键。反正不是对你负责,你不是她的利益所在。
她是对学校领导负责的,学校给她发工资。学校领导是对谁负责的?对不起,也不是你,他们是对更上一级的领导负责的。层层递进似乎没有尽头,但是其实也有,尽头就在纳税人。官僚机构的收入最终来自纳税人。
你是纳税人吗?学生一般来说都不是。那你的父母总是纳税人吧?一般都是。不过税收来自四面八方,没有专款专用这一说,学生父母交过的税跟其他税一同汇总到税务机构,最终分发到每一位食税人员手中。帐是算不清楚的,在这种逻辑中,学生家长处于既是消费者又不是消费者的叠加态中。
具体到学生跟宿管阿姨这件事上,学生父母作为阿姨们工资最终的付款人之一,在这里起不到任何作用。你能跟阿姨说我父母交了税,你的工资没准儿有一部分就是他们支付的吗?你不能。所以她怎么可能给你开门?
最近发生了几件跟大学有关的事情。一个就是前面举的例子,学生因为宿管阿姨不开门导致误了飞机没能见上亲人最后一面。另一个是女生宿舍不准救护人员上楼救人,只因为学校规定女生宿舍楼不准男性进入,最终那个需要救护的女生是同伴抬下楼的,差点送命,当时阻拦救护人员上楼的是一位值班的女生。
宿管阿姨,值班女生,都是一样的原理。她们不对楼里的学生负责,她们只对学校领导负责,学校领导经过层层递进最终按理说应该对纳税人负责,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付款人不能直接追溯到当事学生或者她们的家长,因为这都是一团乱账。
这就是公地悲剧。
二
公地往往都是一团乱账,但是总归需要一些秩序来维持公地的运行。既然是一团乱帐,那么这些秩序就跟算账没关系,跟最终付款人没关系,只跟税款的直接支配人有关系,只能具体到这里了。那么这些机构是什么样的秩序,就得看这些位直接支配人的需求或者喜好了。
权力与市场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权力代表公地,公地的最终决策人不是付款人。市场代表私产,私产的最终决策人就是付款人,而付款人决策的方式就是决定手里的钱要不要支付。与之相对,权力对面的付款人不能决定自己的钱要不要支付,不付也得付。
当我们想通这里面的区别,在公地领域见到任何莫名其妙的稀奇事都没什么可稀奇的了。
我们看到的只是新闻里的两件事,上过公立学校的人都知道,作为接受服务的客户,我们跟父母在学校教育这件事情上几乎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因为我们没付款,或者只付了少量的款,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不是直接付款人,最多是间接付款人,处于付款人和非付款人的叠加态中。
为什么小学老师能给学生跟家长一起留作业,让家长帮着做手工?家长上了一天班回来还得帮孩子做作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对谁负责、利益在哪的道理。义务教育咱又没花钱,要啥自行车?实际上老师的工资笼统来说是家长支付的,又不是家长直接支付的,还是公地里的一团乱帐。
郭德纲开场前总喜欢说一句“郭德纲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他很清楚自己的钱是哪来的。你看哪个公办学校的老师能把家长当成衣食父母来看待?
三
但是本来还可以有更多选择的。
有人可能会说,本来就有私立学校啊,那么贵很少有人上得起啊。确实有私立学校,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因为私立学校开办也是有条件的。
说是私立学校,他们办学遵循的也是权力的逻辑,而不是市场的逻辑。虽然要跟客户收取高昂的学费,但是有能力允许他们经营或者不允许他们经营的人,并不是这些付钱的客户。
所以有什么可说的,确实本来可以有更多选择的。孩子教育跟你去饭店吃饭都是一样的道理。
饭店的饭菜有各种品类,各种价位,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钱包余额决定吃什么。教育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到各种类型的服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钱包和孩子的需求决定购买什么样的教育。
就像饭店不能总是做到让你满意一样,市场化的运营精细化管理也未必能面面俱到,更何况全国铁板一块无法具体到付款消费者的义务教育。这是事实,规则摆在那里,他们确实更加做不到。
在他们的规则里,那个宿管阿姨有错吗?一点问题都没有。学校规定就是六点半开门,又没说家人重病怎么处理。给家长留作业的老师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上面规定要“素质教育”,“亲子互动”,我们也只是照章办事,我对上面负责,又不对你家长负责。
所以咱也不说规则有没有问题了,总之这样的规则继续运行下去,类似的事件出现再多都不稀奇。
——————
推荐:
现在微信公众号引入算法推荐,喜欢本号的朋友可以把我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最新内容,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下面的标签关注一下,相信你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