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何许人也?为何被誉为自由意志主义第一人?甚至被誉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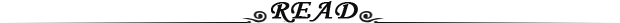
本文本文节选自霍普著作集《伟大的虚构》第三十章,原文为霍普2019年11月23日在奥地利维也纳科堡宫所作演讲,首度发表于纪念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问世七十周年的活动。罗伯特·格罗辛格译自德语原稿。透过此文,我们得以窥见楼下这位大帅哥思想的一鳞半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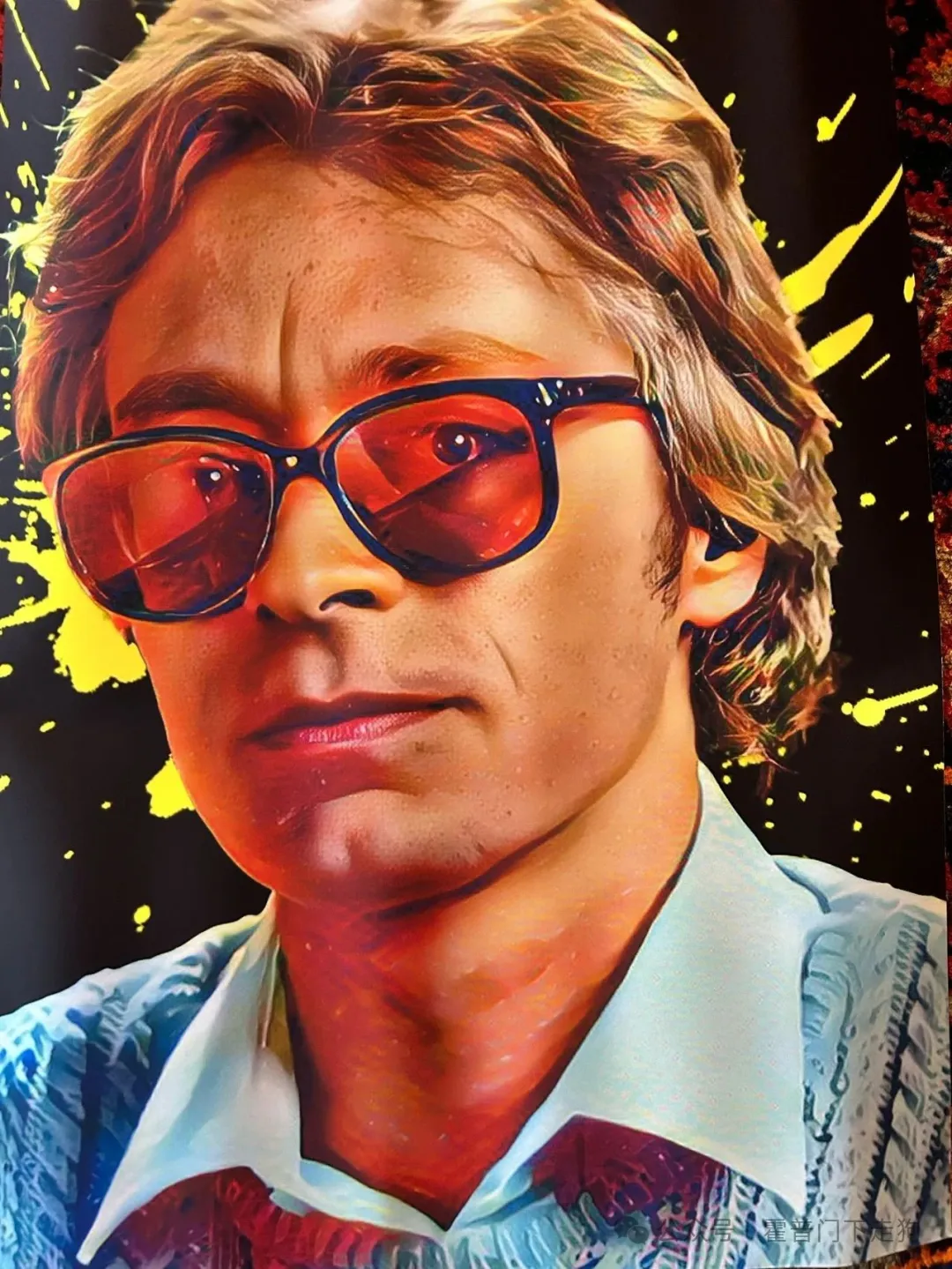
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必须与世界分享个人记忆,这已屡见不鲜。即便年事已高,我也更倾向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生活中的私事与经历,而是留待私下交流时提及。
但在此次活动之际,我想向你们讲述我思想的蜕变历程:谈谈自己如何从一个顺应时代的孩子,在遇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奥派经济学后,蜕变为思想上的异类——有人甚至会说,成了危险的疯子——如同穿越时空的来客。为此,回溯些许个人生命轨迹或许是合适的。
我于1949年出生于战后的德国,恰逢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鸿篇巨著《人的行动》问世。时隔近三十载,我方得邂逅此书,它对我的思想轨迹产生了决定性塑造。而今日,在此特殊时刻,这部著作将首度以德语译本之姿面世于世。
我的父母都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地区的难民,战后他们流落到了西德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West germany)的一个小村庄。我父亲是一名自营裁缝师傅——这一点我和罗兰·巴德尔(译者注:Roland Baader,德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生)很相似,他父亲也是裁缝师傅。我父亲战后从战俘营出来之后,没有回到被苏联占领的家乡。
我母亲后来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她的家族在1946年被苏联当作所谓的东埃尔比安容克(eastelbian Junkers)剥夺了财产,被迫离家弃田,只背着行囊就被赶了出来。在我出生七年后我们搬到附近的县城之前,我们一直生活极度贫困,在狭小的作坊式公寓外有一间户外厕所。
但小时候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相反,我记得自己作为一个小村庄男孩度过的最初几年非常快乐。从50年代初开始,多亏了父母的辛勤劳作以及他们毕生奉行的坚定自律的节俭习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逐年好转。
在我父母家中,《汉诺威报》的地方版是常备读物,每周一《明镜》周刊也会被带回家。家里还有不少书籍,有莱辛、歌德、席勒、克莱斯特和冯塔纳等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有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马克斯·弗里施、伯尔和格拉斯等的现代文学作品。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德国、欧洲和古代历史的著作,以及各类工具书和地图集。我的父母自己就是爱读书之人,他们也一直鼓励我阅读,相比文学,历史总是更让我着迷(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在我十六七岁之前,家里都没有电视机。但我的父母并非知识分子,无法在阅读方面给我指导,也没法训练或提升我的判断力。我对我在文法学校的老师们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几乎都来自经历过战争或战前的那一代人。
学校的历史课增强了我学习历史的兴趣,生物课让我关注到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和动物行为学,而一位新教神学家讲授的宗教课程则首次唤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
然而,正是这种对哲学问题日益浓厚的兴趣,也导致我在思想上愈发不满与迷茫。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所得到的许多答案和解释似乎很随意,更像是观点而非知识,相互矛盾或缺乏连贯性。
这些矛盾和争议从何而来?依据哪些标准有可能解决和判定它们?还是说某些问题或许根本没有明确答案?但最重要的是,我渴望某种知识体系化的东西,一种对所有事物及其关联的整体认知。
正是这种需求以及寻求解决方案的渴望,使我在最初几年成为了典型的时代产物:那是学生反叛的时代,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我中学最后两年,在1968年达到顶峰,而我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大学生活,这个时代的精神产物后来被称作 “68一代” 。
受学生反叛运动领军人物的影响,我先是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著作,随后又钻研新左派理论家,即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如马尔库塞、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满心以为能从他们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我(暂时地)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不过我并非前东德所践行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我通过定期探亲,亲身体验过这种社会主义,其糟糕、可怜的短缺经济以及无产阶级领导人都令我厌恶。
相反,我成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该理论据称由一群睿智的哲学精英引领。就这样,尤尔金·哈贝马斯Jür gen Habermas)成了我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老师及博士论文导师。
当时,他是新左派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而如今则是社民主义的国家主义以及政治正确的道德作秀的头号权威、大祭司。1974年我获得博士学位时,我的社会主义阶段当然早已结束,而我那篇关于认识论主题——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的博士论文,与社会主义或“左派”毫无关系。
在短暂的左派阶段之后,我又经历了同样短暂的“温和”阶段。此时,我的求知欲不再聚焦于法兰克福学派,而是越来越多地投向维也纳学派。更确切地说,是以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为中心的所谓维也纳圈子,而尤其关注处于这一逻辑实证主义圈子边缘的卡尔·波普尔的哲学。
波普尔哲学的核心观点,可能是迄今为止,仍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世界观,在非学术领域尤其如此,其核心观点包含以下双重论断:所有关于现实的陈述都具有假设性质,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被经验反驳或证伪。
反之,所有非假设性的、先验的或确定性的陈述,即原则上不会被证伪的陈述,都是与现实无涉的陈述。
我绝无意接受这一论断的普遍性。(顺便问一句:这是一个假设性陈述还是一个确定性的陈述呢?)甚至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我就接触到了保罗·洛伦岑(Paul Lorenzen)以及所谓的埃尔朗根学派(Erlangen School),他们的观点让波普尔论断的有效性,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有效性,显得十分可疑。
为了检验一个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难道不是首先需要收集和测量数据并进行对照实验吗?关于测量仪器的构造以及对照实验实施方法的知识,难道不是在方法上先于假设检验吗?而且,假设的可证伪性难道不是源于测量仪器构造和实验方法的不可证伪性吗?
如今,我认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比当时所认为的更高,但此刻并非探讨这个主题(或任何高深哲学)的时机。当时(和现在一样),我主要的兴趣在社会科学领域,就这方面而言,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我愿意追随波普尔的观点。
和波普尔一样,我认为社会科学的陈述通常是假设性的,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如果……那么……”式陈述,而且如波普尔所说,实际的社会研究必须是“渐进式的社会工程”。
人们必须始终对假设进行检验,要么暂时证明它们(但永远不是最终定论),要么证伪并修正它们。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不可证伪的陈述,尤其是那些与现实相关,即关于真实对象的陈述。
如今我认为,波普尔的这一论断看似对经验如此包容且开放,实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我觉得它简直是灾难性的,甚至极度危险。
首先,举一个日常经验中的小例子来证明其错误。没人会想要对“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一陈述进行证伪。
相反,我们将其视为一个“绝对正确”或“先验”为真的陈述。然而,它无疑与现实相关,每一个犯罪惊悚片爱好者都明白这一点。因为如果迈尔先生于2019年1月1日在维也纳被刺身亡,而米勒先生当时在纽约,那么在这个案件中米勒先生就不能被认定为凶手:不仅是假设上不能,而且是明确且绝对不能。
这一陈述构成了所谓不在场证明原则的基础,该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为我们提供可靠的帮助。
我在撰写关于社会学与经济学基础的晋升资格论文时,彻底与波普尔主义决裂。一方面,我清楚地认识到,在解释人的行动时,原则上离不开选择、目的或目标、手段、成功或失败等范畴,而自然事件和自然过程 “原本如此”,必须从因果关系角度进行解释,无需涉及选择、目标、手段、成功或失败。
另一方面,不太明显但意义却无比重大的是,我意识到人的行动科学中有一个分支——经济学(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不同),在这个领域,人们完全可以做出绝对肯定的陈述和判断,也就是说,无需进行测试就能知道事情的结果,而是从一开始就先验地知晓结果,并能够确切地做出预测。
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诸如货币数量论之类的观点,该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每单位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对我来说,很明显这一陈述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不可能被任何 “经验数据” 证伪,而且它还是一个与现实有明确关联、关乎真实事物的陈述。
但我遍阅当代文献,无论是左派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著作,还是右派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作品,坦率地说,整个经济学界都痴迷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或波普尔主义哲学。
根据这些哲学观点,这种绝对正确且与现实相关的陈述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在科学上是不可接受的。对他们而言,这一陈述要么仅仅是一种同义反复,即由其他词汇构成的对词汇的定义(与现实毫无关联),要么就是一个有待检验且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假设。
然而,最初因这种明显差异产生的思想上的紧张与困惑,很快便烟消云散,我对此非常满意。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我辗转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读到了米塞斯《人的行动》。
米塞斯不仅证实了我对核心经济学陈述逻辑性质的判断,还构建了一整套绝对正确或先验的论述体系(即他所谓的行动学),并阐释了源自维也纳的实证主义哲学的谬误及灾难性后果。作为他们的同时代人,米塞斯对这些哲学的核心人物十分熟悉。
发现米塞斯的著作,紧接着又接触到他美国学生的观点,尤其是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思想,一方面,让我在思想上如释重负——终于有了期待已久的对所有事物完整、连贯的概述,这是一座人类知识的宏伟架构!但另一方面,这也让我满心愤怒与失望,导致我与学术圈的大学事务以及主流舆论渐行渐远。
这种矛盾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是思想上的确定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疏离感日益加深——可以通过米塞斯-罗斯巴德学派(即所谓的奥地利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揭示的一系列绝对或近乎绝对的陈述示例来阐释和说明。
对于以下每个示例,都有更详细的解释,以说明相关陈述在多大程度上并非波普尔意义上可证伪的陈述。但在此我只是相信,这种情况往往能即刻凭直觉理解,而且无论如何,各种示例集中展现的力量足以让人认识到,人们完全不必为了知道事情的结局(以及明确知道事情肯定不会怎样结束)而去尝试容忍一切。
例如,前面提到的货币数量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提升社会繁荣程度是不可能的。不然又该如何解释,尽管存在随意增发纸币的可能性,但某些地方的贫困状况却依然照旧呢?
货币数量的增加只会导致既定福利财货储备的重新分配。它使最早拿到新增货币的人受益,而牺牲的是最后和较晚使用新增货币的人。
让我接着列举一系列具有类似性质,即绝对肯定或近乎绝对肯定性质的陈述。
人的行动就是利用稀缺资源有意识地追求被视为有价值的目标。
没有人可以故意不行动。
每个行动都旨在提升行动人的主观幸福感。
对于同一种财货,人总是偏好更多数量而非更少数量。
借助给定的手段,人总是偏好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达到既定目标。
生产必定始终先于消费。
只有那些储蓄的人——花的比挣的少——才能永久增加他们的财富(除非他们盗窃)。
今天已经消费掉的东西,明天不可能再消费。
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管制,如最低工资,导致无法出清的过剩,即非自愿失业。
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管制,比如租金上限,会导致短缺,造成租赁住房持续供不应求。
在经典社会主义中,没有生产要素私有制,就不可能有要素价格;没有要素价格,就不可能有经济计算。
税收——强制性收费——是收入创造者和/或财产所有者的一种负担,会减少生产和资本形成。
任何形式的税收都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因为任何税收都会造就两个利益冲突的不平等阶层:一方面是(净)纳税人,对他们而言,税收是一种负担,他们力求减轻;另一方面是净税收受益者,确切地说是税收消费者,对他们而言,税收作为收入来源是令人欣喜的,他们反而力求尽可能多地增加税收。
民主——多数人统治——与私有财产(个人财产与自主决定权)不相容,会导致渐进式社会主义,即持续的再分配以及对所有私有财产权的逐步侵蚀。
任何靠税收补贴维持的活动,比如无所事事,或从事那些没有客户愿意付费购买其成果的事情,都会因补贴而得到进一步鼓励和强化。
任何对自己举借或参与举借的所谓公共债务无需承担个人偿还责任的人——就像如今所有的政客和议员那样——都会为了自身眼前利益,轻率且毫不犹豫地举债,从而损害与己无关的未来公众的利益。
任何凭借国家权力掌控某地区货币发行垄断权的主体,如所有所谓的中央银行,都会利用这一特权。即便增加货币供应量从总体上绝不可能提升社会繁荣程度,而仅能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他们仍会为自身及直属机构和最紧密商业伙伴的利益,印制越来越多的新货币。
最后还有: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要像所有国家实际宣称的那样,在某一区域拥有武力使用和司法管辖的垄断权,就会加以利用。也就是说,其不仅会自行实施暴力,还会凭借自身作为最终法定代表的身份,将自身的暴力行为宣称为合法。
在私人与该机构(国家)代表发生的所有冲突和纠纷中,判定善恶、当事人有罪或无罪的,并非独立、中立的第三方,而始终无一例外是该机构的雇员,即其中一方(国家)的依附性代表,由此产生的结果自然是偏袒且可预期地“支持国家”。
诸如此类绝对肯定或近乎绝对肯定的陈述清单可以轻而易举地继续罗列下去,但现有的内容应该已经足够长,足以让人看出社会科学的这些基本见解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显然,这些见解与社会现实公然冲突。在现实中,存在暴力垄断、货币发行垄断、税收、纳税人和税收消费者、靠税收补贴的闲散与无用之举、多数人统治(民主)、公共债务、无需担责的政客和议员、资本消耗(不储蓄只消费)、财产再分配、最低工资和租金上限。
不仅如此,所有这些行为和制度并未受到持续批判。相反,几乎千篇一律地,各方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正确、有益且明智,同时加以反复粉饰与奉颂。
这些见解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对比所产生的天渊之别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通俗来讲:我自己一开始就被完全惊的目瞪口呆,而且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世界一种公然的疯狂甚嚣尘上。我震惊于自己竟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才得出这个其实显而易见的认知。
这种疯狂状态显然有两个原因。其一纯粹是人类的愚蠢。尽管人们原本追求的目标或许是善意的,但在手段的选择上却犯了错。例如,试图通过设定最低工资来应对失业问题,或通过租金上限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皆愚蠢透顶。
期望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实现更普遍的繁荣,或者在没有增加储蓄的情况下靠扩大信贷来推动经济增长,亦是愚蠢。引入民主制度作为保护财产的手段同样愚蠢。
指望通过建立一个武力使用和司法管辖的垄断机构(即国家)来减少暴力,甚至实现正义,即公正地解决冲突,更是蠢不可及;因为税收,即武力的威胁和使用,以及在冲突解决中的偏袒,是任何国家的基本特征。
但造成这种疯狂局面的绝不仅仅(很遗憾)是愚蠢或无知,还有蓄意的欺骗、谎言与欺诈。也存在这样一些说谎者和骗子,他们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他们知道,上述措施和制度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带来那些头脑简单的同时代人所期望的良好结果,但他们却仍然,甚至恰恰因此而大力宣扬和支持这些措施与制度,因为他们自己、他们的朋友及追随者能够从中获利——哪怕这是以牺牲他人利益并让他人痛苦为代价。
当然,我很快就清楚了哪些人、哪些圈子是这些骗子及其爪牙。通过对米塞斯及其思想流派的研究,我还明白了另一件事:为什么波普尔主义尤其在这些圈子里广受欢迎并被热情宣扬。因为不仅是这种哲学允许将任何疯狂的断言都视为在假设上有可能成立,而且允许对任何无稽之谈进行尝试。
相反,与它所宣称的对经验的接受能力和开放性完全背道而驰,它还允许用蹩脚的借口来保护任何无稽之谈不被反驳。如果最低工资没能减少失业或贫困,那是因为工资还不够高。如果货币或信贷扩张没有带来更多繁荣,那是因为规模还太小。如果社会主义带来的是贫困而非繁荣,那只是因为实施者选错了,或者因为气候变化或其他一些“干预变量”从中作梗,等等,诸如此类。
然而,如前所述,所有这些知识、理解,以及我在接触米塞斯的著作时所体验到的内心平静、满足,甚至喜悦,都是有代价的。一旦你理解了米塞斯的思想,并学会以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世界,你很快就会注意到,至少如果你承认的话,在很多方面你会相当孤独和孤立。
不仅要面对所有这些政治骗子的反对,还要面对他们众多爪牙的抵触,尤其是几乎完全靠税收资助的整个学术-大学体系,而我还试图融入其中。学术生涯即便并非毫无可能,也肯定困难重重。需要极大的勇气、抗争的意愿以及作出牺牲,才不至于辞职或放弃。
在德国——更不用说奥地利了——当时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我决定移居美国。就这样,米塞斯不仅成为我学术上的榜样,也成为我个人人生道路上的楷模。
米塞斯在奥地利未能获得一份常规的学术工作,在国家社会主义者掌权后,他被迫移居美国。即便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他依然难以站稳脚跟。但他的勇气和抗争意志从未被磨灭,他设法让自己的著作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学生,尤其是才华横溢的穆瑞·罗斯巴德。
罗斯巴德一生也是命运多舛,其学术生涯颇为坎坷。但正是罗斯巴德在美国对我关照有加,帮我获得了教授职位,还尤其将我引荐给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院。该研究院由卢·罗克韦尔于1982年创立,在罗斯巴德担任学术总监的激励下发展起来。
从根本上说,正是得益于米塞斯研究院的努力,像今天这样的活动才能再次在奥地利举行。从其草创初直至如今,我与该研究院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无与伦比的卢·罗克韦尔的领导下,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在全球颇具影响力且人脉广泛的机构。
多亏了他的努力,如今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名字与著作,相比他们在世时,知名度大幅提高。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米塞斯或罗斯巴德的追随者。我自己的著作如今也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还有一个例证可以表明奥地利学派自那时起取得的进展:我最近在莫斯科举办讲座,竟有1500人参加,甚至因场地不足,不得不婉拒几百人。
尽管取得了这些不可否认的进步,但显然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米塞斯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在学术领域仍处于边缘地位。事实上,尤其是作为一名“奥派”,完全有理由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感到悲观,至少在中短期内是如此。
因为我们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之前提到的那种常见的荒谬,又因政治正确的疯狂教条,以及幼稚的所谓 “气候保护者” 那病态的、近乎宗教狂热般的气候狂热,而进一步加剧。
面对这些情况,你常常无所适从,不知是该愤怒地长啸痛哭,还是干脆一笑了之。
然而,如今米塞斯学派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当真理最终胜出——因为从长远来看,唯有真理才能行稳致远——那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辉煌时刻也将随之到来。
我们必胜!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