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全方位侵蚀和败坏教育、文化、家庭和个人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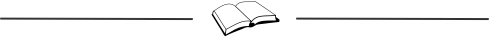
苏联的消亡具有地缘政治影响,并触发了地球另一端的灾难性进展:古巴在经济上依赖苏联的补贴和帮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陷入严重的经济低迷。
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必须寻找一个新的领主,以便牺牲其利益来让古巴的政治特权阶层可以活下去,而他在自己家门口发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
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拉丁美洲的苏联。
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圣保罗论坛(the Forum of São Paulo),它成立于1990年,是拉丁美洲左翼政党和组织联盟。
该论坛的宗旨是讨论柏林墙的倒塌和提出新的左翼策略。
同样,葛兰西的理念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左派企图获得对教育、文化制度和大众媒体的控制权,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智识霸权。
那些控制了文化和大众媒体的人,需要的残酷武力或暴力威胁要少一些。
根据米莱的意见,论坛的计划设想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文化战争,它关乎文化霸权之取得。文化战争意在让左派政党直登权位。一旦在位,国家资源就可用于左派的文化战争。
第二个阶段是实行管制,它旨在伤害资本主义制度。
第三个阶段以征没和国家化告终。
这一图景在委内瑞拉最生动地实现了,委内瑞拉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随着乌戈·查韦斯1998年当选,委内瑞拉成为首个参与圣保罗论坛的左翼政党当政的国家。
在此次成功之后,论坛成员迎来了一波的选举胜利:
2002年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在巴西当选,2005年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Vazquez)在乌拉圭当选、2005年埃沃·莫拉雷斯(Eva Morales)在玻利维亚当选、2006年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智利当选、2006年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在厄瓜多尔当选,2008年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在巴拉圭当选、2009年毛里西奥·富内斯(Mauricio Funes)在萨尔瓦多当选和2011年奥良塔·乌马拉(Ollanta Humala)在秘鲁当选。
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一致的是,圣保罗论坛不再将话语聚焦于经济。
柏林墙倒塌后,资本主义的经济优越性已然很明显。
自由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比不自由国家更高。
相反,左派聚焦于正义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
捍卫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被刻画成自私无情、只关心效率的人。
另一方面,左派是有同情心的,利他的,心里想着穷人。
在关于正义的辩论中,左派拿出了最根本的价值观:公平。
他们以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了剥削。
如前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早在十九世纪初就从理论上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
从经验上,它也被归结为荒唐的。
工人的生活水准大幅增长。
此外,那些在资本主义中逐利的人也给他们的同胞做了好事。
赚了钱的人利用社会资源让其同胞受益。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比社会主义更有效率,它也是唯一公正的制度。
自由意志主义者已经从理论上、经验上和哲学上赢得了这场辩论。
尽管如此,左派还是实现了文化霸权。
他们不谈经济,而是谈论政治认同、性、性别、种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将差异政治化。
左派诉诸诸如嫉妒、怨恨和仇恨这类本能直觉,这促成了他们的成功。
左翼理念主导社会,因为左派懂得如何领导和赢得文化战争。
左派意识到了文化战争的重要性。
在可能出现转向之前,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承认,他们在文化战争中失败了。
它不仅关乎撰写科学论文和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而是需要一场文化战争,通过诉诸情感来深入普通民众的心智。
其工具是媒体、教育机构、文化场所和有影响力的人物。
而在文化战争的背景中——正如圣保罗论坛所展示的那样,左派也理解这一点——人们需要在政坛中有一个立足点。
要不然,国会中的政客就会为所欲为,无论他们在国会之外是不是丧失了一切理论的、经验的和伦理的理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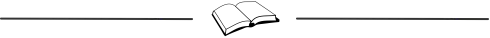
左派在文化战争中取得了成功。
长时间的进军,现在硕果累累:性别意识形态、激进女性主义、性少数群体特权、气候癔症和社会正义咒语。
这是通过种种制度实现的,即在媒体、教育机构和国家中传播社会主义理念和觉醒主义,摧毁资本主义的文化支柱。
在左派的霸权叙事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雇主与工人的阶级斗争已经退居幕后;它如今支持的是所谓的族群冲突、男女冲突和人与自然的冲突。
特定族群的受害状态,被用于优待这些群体,授予他们特殊的权利和扩张国家权力。
这场文化战争的结果对左派而言一直如此成功,它是一种“虚无主义、自我感觉良好的享乐主义和反基督教的文化”(罗斯巴德2000b,第920页)。
一种平等主义的、极端女性主义的、无神论的、气候迷狂的和反人类的文化。
伦理和道德是纯粹主观的,不存在不朽的规范、原则,不存在自然法。
道德决定源于个人偏好。
每个人都应该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时(并自相矛盾地)认为,“仇恨言论”或歧视受害群体是严重的不道德(同上,第176页)。
否定可以通过理性对话和证明发现的,可被普遍认可的客观真理的存在。
只有主观的真理和某种社会性的阶级、种族或性别取向的真理。
剩下的就是为各个群体声言其各自的真理而斗争。
作为文化战争的结果,描述政治上可接受的举措的公共舆论,即奥弗顿窗口(Overton window)也向左转。
[译注:奥弗顿窗口(Overton Window)是由美国政治分析师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提出的理论,指特定时期内社会主流能够接受的政策或理念的范围。超出该范围的观点被视为极端,而通过舆论引导、文化渗透等手段可推动窗口移动,使边缘思想逐渐合法化。]
习惯上被认为是政治光谱中间位的意见,现在被归类为极右,或右翼极端主义。
文化战争甚至更为复杂,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而是生活在所有生活领域都受国家巨大影响的社会中,国家通过税收、监管、补贴、教育体系和媒体实现这种影响。
不存在公平竞争(level playing)。
国家的存在本身就对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
通过影响教育和媒体,以及由于国家本身的存在,国家结构性地促进了国家主义理念和为国家的必要性提供了理由。
再分配计划和政府的不兑现货币(它刺激了债务的发生)影响时间偏好和工作伦理。
福利国家降低了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成本和风险,它有利于这种生活方式的蔓延。
国家从家庭、教育和公民生活中夺走的传统职责之多,前所有未,因此形塑了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发展。
公司复制和强化了这种国家文化价值观。
首先,政治精英对公共舆论的塑造长达数十年之久,然后,私人公司通过雇佣员工和审查违反流行风潮的意见,接管了监督舆论政治正确走廊的任务。
国家在文化战争中是最强大的行动者,它在文化方面是不可能中立的。
归根结底,公立学校、国家媒体、当局应该讲何种语言?
它们应该使用性别语言吗?
在学校中可以将私有财产原则作为文明的根基来捍卫和弘扬吗?
还是说,促进动摇私有财产的“社会正义”原则更好一些?
应该有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来补贴不养孩子的生活方式吗?
企业家和私人个体在作决策时会受到公共舆论和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公共舆论和文化是国家塑造的。
这种影响是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发生的。
在做这件事时,国家并非必须将报纸直接国家化。
对国家来说,影响人民的心智、思想、价值观和信念就足矣。因此,不需要直接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可以优雅地授权给私人部门来做。然后,就不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尽管形式上,是诸如Facebook或YouTube这样的私营公司在审查拥护。
它们是私营公司,但是,它们已经适应了被国家影响了数十年之久的觉醒文化。
国家的这种影响源自它的本质,因为国家本质上就是极权的。
国家希望独立于公民传统和民间机制,以便控制社会的所有方面。
这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国家文化实现的。
为了给出一个国家文化的极端案例,我们可以看看纳粹统治下的文化。
让我们设想一个客栈老板在1938年挂出一个告示:“犹太人不得入内。”
尽管这家客栈是他的私有财产,但这个拒斥犹太人的决定,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个体的决定,而是一个价值观受国家影响,其顾客也受国家文化影响的个体的决定。
国家对文化的影响是多重的,包括国家媒体的资讯和宣传。
但是私营媒体也会受到许可制、监管、政府广告、专访、获取政府信息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机会的影响。
可以预期,无需直接的国家干预,私营公司就会服从。
在这种预期的服从中,公司会做某些事情,例如预先筛选要发布的信息,因为他们会假定一些不利因素,例如政府监管、公司形象受损、失去订单等等。
监管、税收和政府支出会影响人心、慈善、社交互动和时间偏好。
国家货币制度对物质主义、自私和短期思维的影响也不应忽略。
受国家控制和资助的正规教育的影响尤其深刻。
此外,福利国家降低了特定生活方式的成本,从而促进了享乐主义和自私。
国家养老制度为一种不为建立生儿育女的传统家庭出力的生活模式提供了支持。
这是因为国家养老制度强迫有孩子的家庭照顾那些没有孩子的老年人。
通过接管家庭和教会的任务,国家削弱了它们的社会意义,从而也削弱了这些制度传播的价值观。
因此,数十年间,一种国家的世俗的和去基督教化的文化开始出现和发展。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