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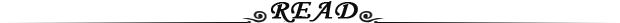
截至目前,本人已成功翻译了霍普的四部著作,包括《自由意志主义“右”对了》(6万字)、《资社理论》(16万字)、《伟大的虚构》(44万字)和《经济、社会与历史》(12万字),以及金塞拉博士的《自由社会的法律根基》(55万字)、费特的《资本、利息与租金——分配理论文集》(24万字),和森霍尔茨的《通胀时代》(14万字)与《欧洲该如何存续》(20万字)。此外,我目前正着手翻译《致敬萨勒诺文集》。我将在此连载这些卓越的著作,若有意先睹为快的朋友,可通过添加本人微信号(ls13957681810)获取电子版本,打赏全凭心意(红包大小与诚意成正比)。
我个人深信,霍普是古今最伟大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极有可能也是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门格尔、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思想传承的奥派当代领军人物,他在超越休谟“is”与“ought”难题的基础上,为自由意志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使自由主义成为一门科学,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尤其是他对民主的祛魅,发人深省。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本文选自霍普的讲座集《经济、社会与历史》第五章,探讨宗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角色。意识形态是统治的基石,而宗教无疑是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鉴于本章篇幅较长,我将分三部分逐一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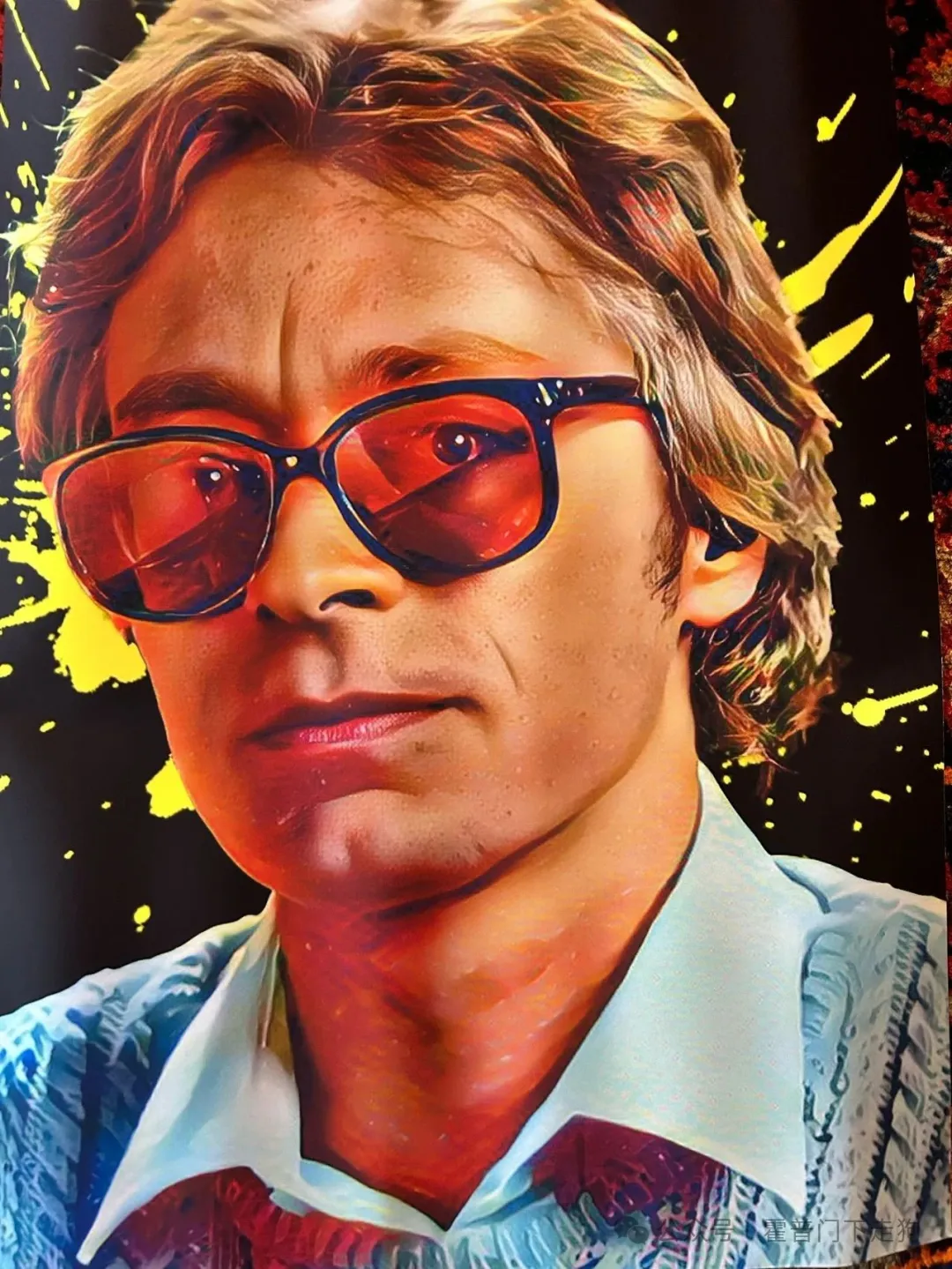
在谈完同样对经济发展不太有利且事实也证明如此的伊斯兰教之后,我们现在将视线转向儒家思想。
我们必须坦然承认,儒家思想显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它对科学研究和探索秉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要知道,大约在1500年之前,中国显然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
儒家思想的世界观完全是入世的,且完全着眼于现世。它没有拟人化的神的概念。它确实提到“天”,但“天”是某种非人格化的事物。
这与我们所想象的具有某种男性形象的上帝毫无关系。实际上,他们没有神灵的概念。他们也不承诺有来世。这可能是优势,也可能是劣势: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其他宗教如何描绘来世。但无论如何,儒家思想不承诺来世。
儒家思想完全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态度还体现在,对他们来说不存在“神迹”,这与基督教形成对比,我们知道,基督教承认存在“神迹”。对儒家信徒而言,“神迹”并不存在。
也就是说,一切都能够合理解释。相应地,也不存在圣人这样的概念。孔子本人既非神,也非先知。孔子只是一位领袖、一位老师。正因如此,有些人甚至怀疑将儒家思想称为一种宗教是否合适。
也就是说,没有神,没有先知,我们能合理地将其称为宗教吗?此刻,让我给你们引用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Stanislav Andreski)关于儒家思想的一段话。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是一位波兰社会学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英国任教,他是极少数非左派的社会学家之一。
还有其他几位像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和赫尔穆特·舍克(Helmut Schoeck)亦是如此。如我所说,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非常有趣。他是这样论述儒家思想的:
如果我们想依据与科学发现的契合程度来给各宗教排序,那必须把儒家思想远远排在首位。
事实上,其理性主义和现世的世界观,导致一些学者否认它是一种宗教。尽管如此,从词源学意义上讲(“宗教”一词源于拉丁语“to bind”,意为“约束”),它无疑就是一种宗教,因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它无疑构成了一种纽带,将数以亿计的人联结在一起。
然而,如果我们把拟人化的神灵概念和对来世的承诺视为宗教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得出结论: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因为对儒家信徒而言,至高无上的实体是“天”——一种无形且非人格化的力量,而非像在近东诞生的那些宗教中那样,是一个以尘世暴君形象塑造的人格化的神。
当被问及人死后会怎样时,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从未宣称自己拥有任何可被称为超自然或神奇的力量,其追随者在他身后也没有赋予他这类能力。儒家信徒不期待“神迹”,也无圣人概念,他们尊崇其创始人,不是将其当作神灵,而是视为一位伟大的老师。
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天然兼容的世界观。它非常强调孝道与家庭团结,这在个人突破现有传统进行创新方面,可能会产生某种负面影响,但从原则上讲,孝道和家族观念与资本主义并无冲突。
关于在儒家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创新精神缺失这一点,我再给大家引用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人类成就:对卓越的追求》一书中的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观点。他说:
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这是人类的最高美德,一种集善、仁、爱于一身的品质。这种伦理对于那些手握重权之人最为重要。孔子教导说:“宽则得众,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的确,要成为 “君子”(儒家思想的另一关键概念),首要的是践行 “仁”。而且,别以为君子只需嘴上重复恰当的陈词滥调就行,孔子补充道:“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由于这种浓厚的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日本的孩子在做人生决策时,也理应首先考虑父母的意愿和福祉,其次是大家庭,最后是所在社区。
相较于西方传统,中国和日本不太鼓励人们不顾一切地追求自我实现,而在西方,这种追求更为普遍。此外,中国人极为重视学习;中国实行的是任人唯贤的制度,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某种考试制度,跻身社会顶层。
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个选拔高智商人才的社会,因此也倾向于将民众与世俗权力联系在一起。由于每个人都有晋升机会,且任人唯贤的制度让谁能晋升、谁不能晋升显得较为公平,所以即便是社会底层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并安于这种制度。
必须指出,中国最终无法与西方竞争的原因之一,在于儒家思想从很早开始就与国家官僚体制紧密相连。
也就是说,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世俗统治者(中国皇帝)与儒家学说、儒家神学(暂且这么表述)的高层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或近乎直接的一致性。
因此,儒家思想很早就与国家权力捆绑在一起,正因如此,其内在的对发明创新的抵触情绪进一步加剧。
我再次指出这一点。儒家思想与国家的这种结合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性思维的缺失。
也就是说,在西方,尤其是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学到要先提出一个论点,然后给出一个反驳论点,接着再给出另一个反驳论点,并努力弄清何为对、何为错,在这种一来一回的无尽过程中相互辩驳,而这种情况在中国极为罕见。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在内华达州我们有很多东方学生),我甚至能在我的学生写批判性文章时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做数学方程式和选择题时总是非常出色,他们什么都记得住,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但当要写像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那种文章时,也就是先提出论点,然后要给出反驳论点,接着必须筛选出哪些论点更强、哪些更弱,并可能以某种方式综合这些内容,他们在这方面就明显表现不足。另一个体现这一点的迹象——这有点属于推测——是,虽然在数学、物理、工程等领域,东方人的占比极高,但在法学院里,他们的人数却明显偏少。
而在法学院,恰恰非常需要这种希腊式的辩论方式,这是我们西方人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的。与他们明显占比过高的其他领域相比,在对这种希腊式辩论有特别高需求的地方,他们的占比却偏低。再次引用查尔斯·默里对此观察的一段话。他谈到东亚时说:
在科学领域,不认可公开争论,这损害了东亚科学构建累积性知识体系的能力……中国科学史是断断续续的,偶尔会有杰出的学术发现,但却没有后续跟进。西方科学的进步得益于热烈、持续、竞争性的争论,其目标就是脱颖而出。
东亚没有相应的文化资源来支持这种热烈、持续、竞争性的争论。即使在如今的日本,自这个国家开始西化一个半世纪后,人们普遍注意到,日本的技术成就远远超过其为数不多的原创性发现。
对于这种差异,一个现成的解释是,通过达成共识和层级式推进取得的进步,与需要坚持自己绝对正确的个人来推动的进步之间存在差异。
当然,你能察觉到在西方,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正确,而他人皆错。
说完儒家思想,接下来我们谈谈犹太教。首先得说,犹太教群体一直规模较小且分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
此外,由于犹太教不热衷于传教,即他们不会主动去四处游说他人皈依其宗教,所以始终保持着小规模,散居各地,影响力相对有限。
有些学者,比如德国社会主义者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他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反对者之一,属于所谓的“讲坛社会主义者”,提出了犹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发明者的观点,但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原因如下。
的确,例如犹太人涌入荷兰、威尼斯以及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后,这些地方开始繁荣起来;而且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后,西班牙走向衰落,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一定表明存在因果关系。也有相反的例子。
比如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恰恰兴起于犹太人被逐出英国到重新被允许进入英国这段空挡时期,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绝非一定需要犹太人的存在。
还有其他一些指向不同结论的迹象。例如,在任何一个犹太人人口占比很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犹太人并非像在东欧那样,作为极小的少数群体被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包围的地方,经济发展往往都不尽如人意。
也就是说,在那些地方,犹太人的存在总是与赤贫相伴。在波兰和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犹太人的数量比在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些先进国家的还要多。
当犹太人开始为科学做出重大贡献时,当然,没人会对此表示怀疑。而这种情况只有在他们作为少数群体,与周围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有所接触时才会发生。
例如,在中东、西班牙,在所谓阿拉伯统治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从18世纪后期基督徒解放犹太人之后。我要强调,犹太人的解放是基督教的成果。犹太人从自身原有的受束缚状态中获得解放,并非靠他们自身,而是借助了外部力量,即基督徒。
可以说,基督徒不再愿意以犹太人过去遭受的那种方式去压迫和对待他们。所以在1800年之前,犹太人取得的成就相对较少,而你所见青史留名者,通常是那些与自己宗教决裂之个体先驱。
传统的东正教犹太教同样要求严格服从家庭和社区,这与在伊斯兰社会所见的情况颇为相似。
在所谓的犹太“隔都”(Ghetto),犹太人实行自我管理,这种自治权通常由外部统治者赋予,作为交换,犹太拉比在内部对本社区成员处以罚款后,会将其中一部分上缴给外部统治者。
犹太人居住在“隔都”,部分原因与他们的一些禁忌有关,比如他们必须居住在距离犹太教堂很近的地方,且在一天中的特定时段不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靠近某些特定场所。如果你是一名东正教犹太人,至少就不能彼此居住得过于分散。
例如在西班牙,情况正是如此。在犹太“隔都”,你们拥有自治权;可以依据犹太教律法,对其他犹太人施加任何形式的罚款或惩罚,但收取的罚款需按一定比例上交给西班牙国王。
于是,西班牙统治者与负责管理犹太“隔都”的拉比之间达成了一种互利安排。当时,“隔都”内的生活几乎完全处于拉比的掌控之下,这与伊斯兰阿亚图拉对民众的控制并无二致。
赚钱是被允许的,在“隔都”外赚钱也没问题,但目的只能是支持对《塔木德》的研习。为了实现这一点,犹太人常常成为统治者压迫当地居民的工具,在波兰和俄罗斯等地尤其如此。
“隔都”外工作的犹太人被统治者当作针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征税员。犹太人被允许如此行事,是因为……马克斯·韦伯称他们奉行双重伦理准则。也就是说,他们对内适用一套规则,对外则适用另一套规则。
举个例子:长期以来,基督徒禁止收取利息,犹太人也禁止收取利息,但对基督徒除外。禁止向其他犹太人收取利息,却可以向基督徒收取,这当然使他们特别适合从事某些职业,比如放贷。
在犹太“隔都”——我马上给你们引用一些相关内容——阅读用现代语言写成的书籍是被完全禁止的。除拉比明确许可之外,即使用希伯来语写作也不被允许。
如今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特别幽默,想想伍迪·艾伦或默里·罗斯巴德便知一二。但在“隔都”内,幽默被视为禁忌。饮食和性方面的禁忌被严格执行。教育完全只限于涉及《塔木德》和神秘主义典籍,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都被排除在外。
任何违规行为都会招致严厉惩罚,甚至可能被鞭笞至死。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犹太人的解放,从那时起,他们所能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功绩,这得益于《旧约》中清教徒式价值观的影响,而《旧约》也是犹太教传统的一部分。
而一旦获得解放,再结合他们自身清教徒式的精神,他们确实成就斐然,于商业一道尤为突出,并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群体。我想给你们读一段关于犹太“隔都”氛围的具体描述:
正如斯巴达没有喜剧一样,解放前的犹太社区也没有喜剧传统——两者的根源都指向严苛的社会控制。再看看对学习的态度。当时的犹太人对知识的追求仅限于宗教领域,且这种宗教研究本身也处于扭曲与僵化的状态。
欧洲犹太人(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区稍好)普遍蔑视甚至敌视一切世俗学问,唯有《塔木德》和犹太神秘主义被允许研读。《旧约》中大量篇章、非宗教类希伯来诗歌、犹太哲学著作均遭禁绝,连提及这些书名都可能被诅咒。
语言学习、数学、科学被严格禁止,地理与历史(包括犹太民族自身历史)更是一片空白。任何微小的创新或温和的批评都会招致最残酷的迫害。
这是一个深陷最极端迷信、狂热与蒙昧之中的悲惨世界。1803年,俄国出版了第一本希伯来语地理著作,其序言无奈地写道:许多大拉比甚至否认美洲大陆的存在,坚称它‘绝无可能’。”
犹太人的贡献始于犹太人解放之后,基本上是从外部开始的。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实际上可以说在某些方面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