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意识形态大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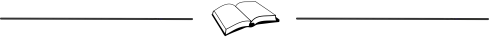
但是,自由意志主义的种种思潮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哈维尔·米莱属于哪一派?
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主要潮流。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拒绝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个人自由不受限制,甚至不受国家限制。
古典自由主义的许多现代代表人物赞成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费尔南德·拉塞尔(Ferdinand Lasalle)轻蔑地称小政府是“守夜人国家”。
捍卫小政府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被称为最小国家主义者(minarchist)。最小国家仅负责捍卫财产权利。
它通过国家警察、国家司法和国家军队来提供内部和外部安全。只有出于此目的而征收的税收才是合法的。在最小国家主义者看来,对贫苦者的教育、医疗、养老或援助,都不是国家的任务。
这些需要可以通过公民社会在竞争中以更物美价廉的方式提供。
最小国家的自由意志主义代表包括诸如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之类的思想家和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样的经济学家。
第二种自由主义思潮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它将自己与古典自由主义区分开来。
它产生于1938年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即所谓的“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Colloque Walter Lippmann)”。
新自由主义作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手而诞生。它以各种形式与社会主义作斗争。
然而,新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最小国家的自由放任理路是有利的。相反,新自由主义拥护强大的国家来设定框架,从而从侧面攻击经济生活。
此外,国家应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国家必须禁止垄断和卡特尔的形成,限制市场力量。
有着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的芝加哥学派,和有着像沃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这样的经济学家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可以归为新自由主义。
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有时候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有多大的吸引力。
因为新自由主义赞成太多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米塞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我越来越怀疑是否有可能在朝圣山协会(Mont Pèlerin Society)中与秩序干预主义(Ordo-interventionism)合作。”
美国的“自由主义”不属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学派。
在美国,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个术语被自由理念的敌人篡取了。
就其内容而言,美国的“自由主义”类似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对自由主义这一术语的重新解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追溯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他来说,自由不仅仅是免于物理胁迫,而且是免于公共舆论和传统的“暴政”。
因此,密尔反对宗教、传统和社会规范。
在这方面,国家从对自由的威胁被改造成自由的支持力量。它必须保护工人和消费者免受企业力量之害。
美式自由主义创造了庞大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性的国家。
因此,美国的自由捍卫者,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再使用“自由主义(liberal)”这个术语,而是切换成“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
在欧洲,“自由主义”一词仍然保留了它的初始含义,今天这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使用“自由意志主义”一词来描述更加逻辑一致和更加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也就是那些想要激进地限制国家的人,例如最小国家主义者,或者那些希望将国家一扫而光的人,即所谓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这是第三种自由意志主义潮流。
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从根本上拒绝国家的存在。他们用伦理理由和经济理由来支持这种立场。
从伦理角度看,为了征税,针对无辜的人民发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似乎是不合理的(unjustifiable)。
国家是像黑手党那样的犯罪组织,所不同的是,国家是法定的,有更好的手段。
经济考虑是以“国家是暴力运用的垄断者”这一断言为基础的。
但是垄断总是糟糕的,即使在它提供安保时也是如此。
它们导致前所未有的价高质次。因为垄断者不会受到竞争恶惩罚。垄断者可以自己决定其服务的价格,他不必调整自己适应消费者的愿望。
根据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意见,所有社会关系都应该是自愿的,非侵犯性的,没有强制威胁的。国家机器意味着系统性胁迫,因此是不正当合法的。
税收是抢劫。
与国家和胁迫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想要市场和自由。
政客不应该自以为是地决定需要做什么事情。
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想要牺牲生产者利益以自肥的政治特权阶层。
在自然的去中心化的公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其自身命运的设计师。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重要代表是穆瑞·罗斯巴德、大卫·弗里德曼、沃特尔·布洛克、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和汉斯-赫尔曼·霍普。
如今,自由意志主义者不仅可以分为新自由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而且可以按照他们的左-右倾向来区分。
诚然,由于过于简单化,区分左和右的方案总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然而,为了让复杂的现实更好理解和节省时间,这种方案也是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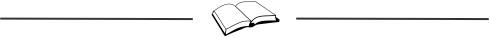
“右翼”一词的使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有些令人遗憾,尤其是在德国。因为今天“右翼”通常被等同于“邪恶”。
另一方面,“左翼”总是与善良、同情、利他和人道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中,左派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优势。
按照公共舆论,它代表了正义和理想。
“右=邪恶”、“左=善良”的定义,不仅在分析上毫无益处,而且具有误导性。
然后,希特勒被归为右翼。事实上,纳粹如今被视为右翼意识形态,正是二战结束后左派的天才之举。德国今天仍然受困于这种黑白颠倒。
至少在安格拉·默克尔总理的政府时代,以及红绿灯政府[译注:2021底-2024年底的德国政府,因其由三个代表颜色分别为红黄绿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联合组成而得名]时代,这种扭曲的致命性更为凸显。
因为对左翼政治的任何批评都是右翼的,从而是邪恶的。
一切非左翼的观点,一切反左派的思想学派都是邪恶的。这种夸张和扭曲让人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左翼政治能够在德国如此昭彰。
很难形成对左派的反对派,因为任何联盟,只要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就会被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是“邪恶的”。右派的联合行动被有效地阻止了。
然而,只是中短期如此。
因为左翼政治的肆意表达,正在制造前所未有的荒唐乱象。
由于陷入左翼思维逻辑和依赖于策略上的成功,左派必须持续地“将右派推到角落里去”。所有那些非左翼激进分子和非觉醒主义者都是纳粹。
从短期看,这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但是从长期看,它会增强反对派的力量。
因为结果将会是文化、社会和经济衰退。
而这不仅导致了阿根廷的倒退,而且,“强制平等(forced equality)”这一左派意识形态核心,也是对自然的反叛。对这种反叛的反动也会在德国出现。
迟早的事。
顺便说一句,米莱也有能力有意或无意让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会成为纳粹的攻击免疫。
他公开表示要皈依犹太教,并定期与拉比阿克塞尔·瓦尼什会谈,他与后者一道学习犹太经典《托拉(Torah)》。
瓦尼什被米莱任命为阿根廷驻以色列大使。
米莱也毫不含糊地捍卫以色列的自卫权。他身为阿根廷总统的海外第一站就是以色列。
他支持以色列国,在加沙战争中尤其如此,这使他赢得了赞扬,但也受到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批评。
但是,是否存在一种有意义的,超越“恶与善”的愚蠢区分的左右光谱方案?
一种让政治思潮及其区别和各自原创观点变得可以理解的方案?一种适用于经济分析的方案?
我们在埃里克·马里亚·里特尔·冯·库埃内尔特-莱丁(Erik Maria Ritter von Kuehnelt-Leddihn)(2009)那里找到了一种很有希望的理路:
“右”代表人格(personality)、垂直性(verticality)、超验性(transcendence)、自由、辅助性(subsidiarity)、联邦主义和多元化。“左”代表集体主义、横向主义(horizontalism)、唯物主义、平等相似性、集权主义(centralism)和简化(simplicity)。
库埃内尔特-莱丁(2009b)从这一定义中得出了左翼意识形态的几个特征:
唯物主义、集权主义、极权主义、福利国家、反自由主义、反传统主义、国家对教育教学的控制、大众媒体的强制一律、废除私有财产或使之相对化(relativization)、憎恨少数派、赞美多数派、民粹主义(populism)、煽动集体歇斯底里、将生活整体政治化、与“特权”作斗争、动员民众,煽动嫉妒。
右派与之对立。
他区分左右的核心是自由与平等的概念。
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由或平等(Liberty or Equality)》《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中,库埃内尔特-莱丁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与平等在政治上是对立的。
自由在右,平等在左。
对人而言,右(right)是真正的正确(right),右就是自由。
只有在自由中,人这种自然的多重谜题(multi-layered enigma of nature)才能发展出人格、自尊和精神成长。
为此,人需要独立。
他需要能够发展和表达自我的空间。
尤其是在生命之初,他需要其家庭的保障。
右派捍卫个人自由,以及自由地、有机发展的制度,其中就包括尊重传统。
它代表自由思考、传统、真正的价值观和关于人性的平衡观点。
人既非恶魔,亦非天使。
左派代表相反的原则,代表统一和平等。
左派憎恨偏离、差异、层级和等级。
然而,自然是不平等的。
平等只能利用胁迫人为实施。
为此,国家是左派喜欢的工具。
只有奴隶是平等的。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希望使统治集团的所有成员都平等。因此,在这个方案中,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在左派这一边。
同时,左派认为西方文化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
阿根廷知识分子奥古斯汀·拉赫在划分自由与平等时补充了另一个维度。
根据拉赫(2022,第400页及后)的意见,左派代表社会冲突,右派代表和谐。
对左派来说,不平等总是意味着等级制度,从而意味着必须由国家来消除的剥削。在家庭、公司、教会和社会地位中都存在着不平等和等级制。
因此,左派随处都能发现剥削和社会冲突,而国家应该支持更多的平等,将它们一扫而光。
所以,左派还站出来反对传统家庭,从而反对黏合社会的纽带。因为家庭意味着等级制。
为了使人人平等,左派希望尽早、尽可能地从家庭手中夺走孩子,并由国家来教育他们。
另一方面,右派认为有机地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是和谐的。
不是每一种不平等都意味着等级制。
而右派根本不认为等级制有问题,如果它是自然的,是自由的产物的话。
不平等是人们必须接受的现实之一部分。
差异是自然和和谐秩序的一部分。
根据右翼的观点,正是有机地、自然的、功能性的等级制首先让社会的和谐运行成为可能。
家庭是最好的例子。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等级制和不平等。
孩子需要负面的权威。
同样的,在教会中,牧师与信徒之间也存在着等级。
从经济角度看,差异也是某种积极的事物。
为了使交换发生,交换双方必须对所涉及的商品有不同的估值。只有甲对X商品的估值高于商品Y,而乙对商品Y的估值高于X,才有可能出现交换。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者从事专业化生产,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那些专业生产牛奶的人会有许多牛奶和更少的衬衫。反过来,那些作为裁缝专业生产衬衫的人同样如此。裁缝将拥有许多衬衫和更少的牛奶。这就使得交换对双方都很有吸引力。
奶农用牛奶交换裁缝的衬衫。双方的处境都改善了,彼此互补。
基于市场的劳动分工是以互补性为基础的,因而也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
不平等不是某种负面的东西,它使互补、自愿交易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得以可能。
另一方面,左派将这些差异视为压迫性制度,例如资本主义、教会或父权制的结果。
左派希望在国家强制权力的帮助下实现人人平等。必然包含等级结构的既有制度要消失:“白纸好画画”(tabula rasa)。
在清扫了等级制度后,左派希望通过社会工程创造它自己的理想。这种左翼建构主义与伦理自决齐头并进。
拥有权威的不是传统价值观、传统规范甚至教会。个人自己决定何为善恶。这种伦理自决的终点是道德相对主义。
个性(Individuality)是左派和社会主义这一端的一根刺。
诸如私有财产、家庭和宗教形式等制度维持和强化了人的个性。
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人作为人回归上帝)强化个性和人格,而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的障碍。
因此,社会主义追求削弱人格和个性,以及宗教超验性和任何定义个性和与平等冲突的等级制。
相反,个人被认为应该适应(伦理或性别的)群体认同。
何为好,何为坏不再是普遍的,而是取决于这些群体之间的动态的力量对比。
左派在为平等而斗争的过程中,不仅反叛生物现实,而且反叛现实的本体架构(ontological structure),反叛普遍性本身。
例如,新马克思主义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要求全盘否定和改造现有的现实架构——以实现其真正的潜能。
左派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为了实现其狂野的狂想而否定现实架构。
然而,平等主义者的狂想有可能摧毁整个他们想要否定和超越的世界。
左派意识形态深度反人类和不道德,因为它否定人和宇宙的架构。
实现左派的狂想意味着摧毁文明。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