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发起了一个讨论,那就是言论自由是不是一种权利?为什么有这个讨论,并不是因为我大号被封禁,而是我看到了一个案件。有一个人,在抖音上制作了一个视频,用影视特效去做了一个炸掉收费站的视频。这事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甚至很多网友不服,还不停地在抖音上发各种用这个特效做的视频。这件事,其实就关系到了关于言论自由权利法理的一个讨论。前天有不少朋友留言了,有不少朋友的留言都挺精彩的。你看,言论中,存在教唆,威胁,命令,造谣、煽动、辱骂、承诺、欺诈等不同的形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将不同的言论进行了区分。比如,被清晰地被大部分地区界定为犯罪的言论行动有:威胁:用暴力威胁达成目的。不管在任何地方,你用暴力威胁他人要求交出财物,这被视为抢劫,而世界上大部分抢劫,基本上并不直接使用武力,因为成本太高,更多的是用语言进行威胁,并展示出武力以证明语言威胁的真实性。如果某人打个电话去航空公司,说飞机上有炸弹,威胁对方,那也是妥妥的犯罪。欺诈:用语言的方式占有他人的财产,这等同于盗窃,因为这种语言的后果就是侵犯私有财产。命令:命令是代表着发出命令者与执行者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双方是共同行动人,当然是有罪的。希特勒是命令发出者,他与党卫军是一个组织,所以命令是需要承担后果的。如同买凶杀人,哪怕买凶者没有支付费用,他是杀人的发起者,策划者,杀人具体事务的安排者,哪天杀,杀谁,那这种语言与命令是一致的。所以买凶杀人,也是需要承担后果的。向政府呼吁加重税收,向政府呼吁使用司法暴力杀害某人;我认为,判断哪种言论会导致犯罪应该遵循如下法理原则 :2、言论对于伤害结果之间,是否是立即、马上、显而易见的威胁这一群人在一个月后,他们实施了行动,那我认为这个言论与结果之间清晰的因果关系不成立,没有构成立即、马上、显而易见的威胁,且言论者并不能预知结果。如果是在游行现场,某人对着旁边的工厂进行演讲和鼓动,那我认为,这一演讲与事后的烧杀抢构成了直接因果关系,形成了立即、马上、显而易见的威胁,且言论者也能预知此后果。所以言论者需要承担后果。在电影院没有火灾风险时大喊着火了,也符合这一法理原则,也应该承担法律后果。其实很多政客发动屠杀,并不一定通过命令,更多的时候,他们通过演讲来煽动军队、或部分民众参与对另一部分人的屠杀。但这些演讲无疑构成了杀戮的一部分。而那些没有构成暴力威胁,或不会导致马上侵害后果的言论,则不存在侵权。比如承诺,我到某一个福利院去,我承诺捐一个亿,事后,我不按此承诺执行,我有侵权吗?没有。这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我们可以批评这一行动不道德,但他不存在侵权的后果,并没有侵犯对方之财产权。有人说,教唆无罪,因为对方也是心智齐全的人,要不要犯罪,他们自己可以进行判断。教唆与犯罪行动之间没有必然之因果关系。比如,某人受到另一人侮辱暴怒当中,旁边人怂勇,不要怂,拿刀砍死他。这个人就立刻用刀砍伤砍死对方,那怂勇者有罪吗?因为教唆者能预见言论与后果的关系,并且言论会与伤害后果之间产生立刻、马上、显而易见的关系,同样,我们可以认为,言论与后果之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相反,如果不是立刻马上的行动,教唆者不能预知到后果,那就不构成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具体来看,这个用特效来制造炸收费站的事情,是否是违法的?制作者在发布视频时,撰写了“炸掉XX收费站”的字样,视频中央就是XX收费站的形象,这一视频构成了对XX收费站直接的暴力威胁。我们再假设,将XX收费站改为机场,改为高铁,我们都可以清晰而明显地判断出,视频制作者在试图制造威胁。这与打电话过去机场说,我准备炸掉你这里的某个航班的飞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在于严重性的程度。而其他大部分这种特效视频,则不构成违法。因为其没有具体的指向,也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暴力威胁的意图。首先,造谣并非信息不明确,如果因为信息不明确发布的言论,那就不构成造谣。因为这是信息模糊导致的。造谣一定要清晰地判断出对方是无中生有,是人为编造信息,并会产生立刻、明显的、具体的、显而易见的伤害。不会产生立刻、明显、具体的伤害的信息,不是谣言,那叫吹牛。比如,某人说明年1月20日,电影院将会着火。这个并不一定会产生伤害,他只是吹牛,只是扮演先知。正如同有少人鼓吹世界末日一样,当然有相信者去准备逃生物品,但大多数人是嗤之以鼻。这种伤害并非显而易见的。来源于信息不明确的信息,也不是谣言。比如发现某种病毒,某人不知道他是什么病毒,也无公开信息渠道让他了解病毒的信息,那他依据个人经验判断,认定为某种病毒,引发什么恐慌,也不是谣言。人类总是需要面对信息的不确定性。如果某企业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有人在网上编造信息说某企业产品吃死了人,这显然是谣言,并会产生立刻的伤害和后果。但如果是某人确实因为服用了某企业的产品,出现了死亡,其家人在信息不明确的情况下,指责该企业产品质量有问题,则是合理的。企业也需要面对不确定性的信息。辱骂不构成侵权,因为辱骂者并不能预知到会有什么后果。辱骂行动与后果之间无法构成清晰的因果关系。不同的人对于辱骂是有不同的感受的。相同的人,对于不同的辱骂也是会有不同的反应的。这是一种纯主观的感受。如果某人因某事直接威胁对方,你再这样,我就杀了你全家。这种言论显然构成了立刻、显而易见的暴力威胁。这种言论显然是违法的。不管对方是否相信他这种暴力威胁,但他这一言论,已在事实上构成了恐吓。这与暴力威胁抢劫本质并无不同。银行职员照样可以不相信抢银行者说出来的话,但这不影响用语言威胁的抢劫性质。假设美国不少民众呼吁加征遗产税,征九成,把富人的财产全部剥夺了,并达成了结果,那这些民众是否参与了剥夺?所以,只能从道德层面上批评他们的行动,而无法在法理上认定其参与了剥夺行动。同样的,撰写种族灭绝理论的学者,也无法预知他理论产生的后果,所以,他们也不构成犯罪,也只能从道德上谴责他。法理上,应该将语言和所有的行动视为同一种行动,因为人类大部分行动就是语言。当语言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明了时,那语言也是犯罪行动的一部分。财产权、人身权是先天性排他的,不会引起产权争议,你拥有了,别人就不可能拥有。因为排他性的存在,所以财产权和人身权本身是不会导致发生对他人的伤害。但言论是人的行动之一,通过语言达成伤害目的的行动非常多。既然是一种行动,那怎么可能构成权利呢?脸书也有权封掉川普的帐号,这是在于财产权派生的契约权。但拜登政府如果用暴力要求脸书封掉川普的帐号,那是拜登政府侵犯了脸书的财产权。现代人民主权理论中,言论自由权是约束政府的,是一种针对政府行动的专项主张,而不是一种普遍认知的权利。也就是说,侵犯言论自由的只能是政府。所谓言论自由权,是规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规则,是以政府存在为前提的。这也说明了一点,这一自由概念是针对政府这一机构的,而不是普遍的权利,实际上要表达的就是民众不应该因为批评政府而有罪。既然不是普遍的权利,就没有必要界定为权利,否则就会导致混乱。今年脸书封川普的号,就导致了认知的混乱。这种认知,就是把约束政府行动的“言论自由”概念扩展到了民众之间的行为规范了。
基于财产权和人身权,才能在法理上达成逻辑一致,并形成定争止纷的法,而搞出来一个什么言论自由权,则让大众陷入混乱,无法对权利进行清晰认知。(今天讲的可能争议会比较多,这个事,确实是个难题,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欢迎批评)
![]()
关注本号,在公众号输入“99”将收到我送给新朋友的十本经济学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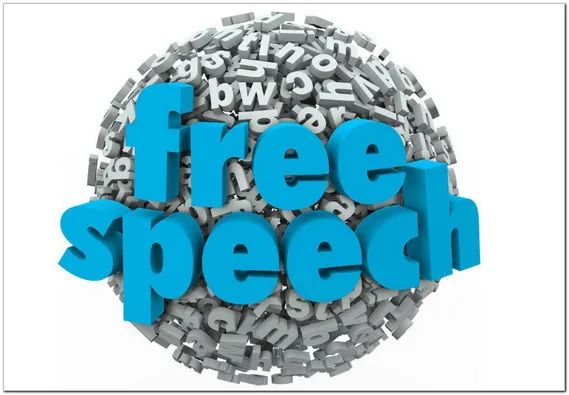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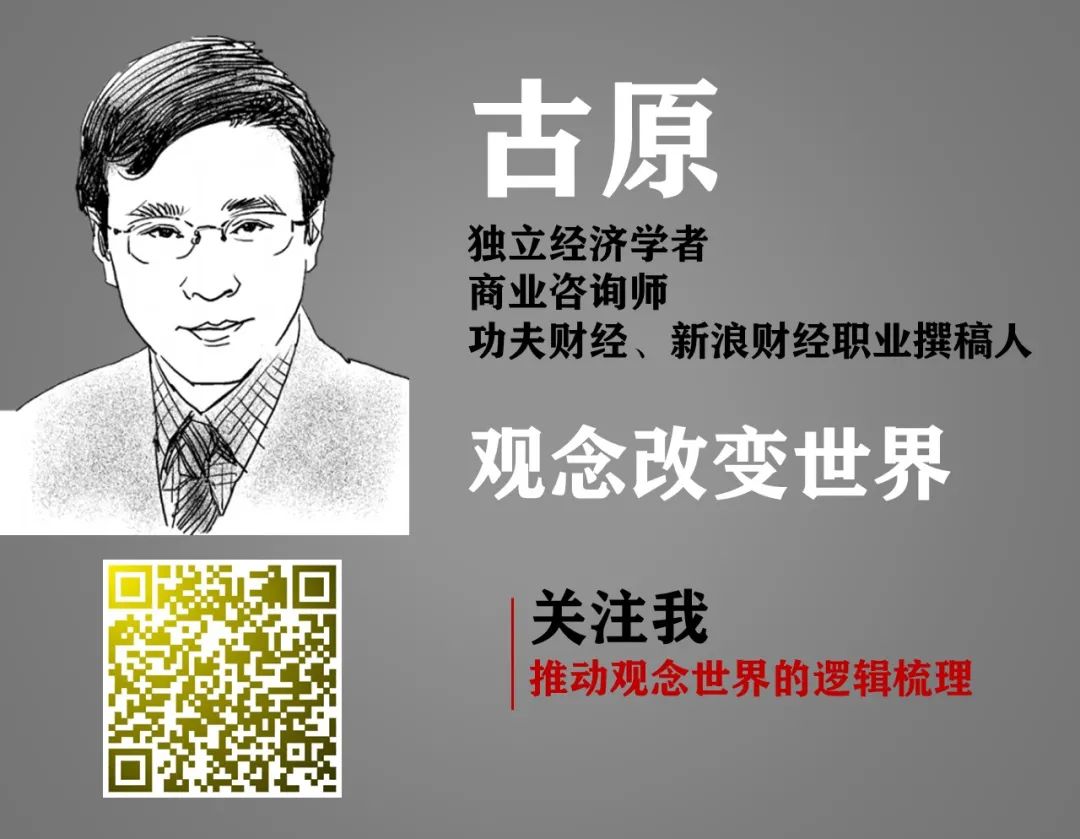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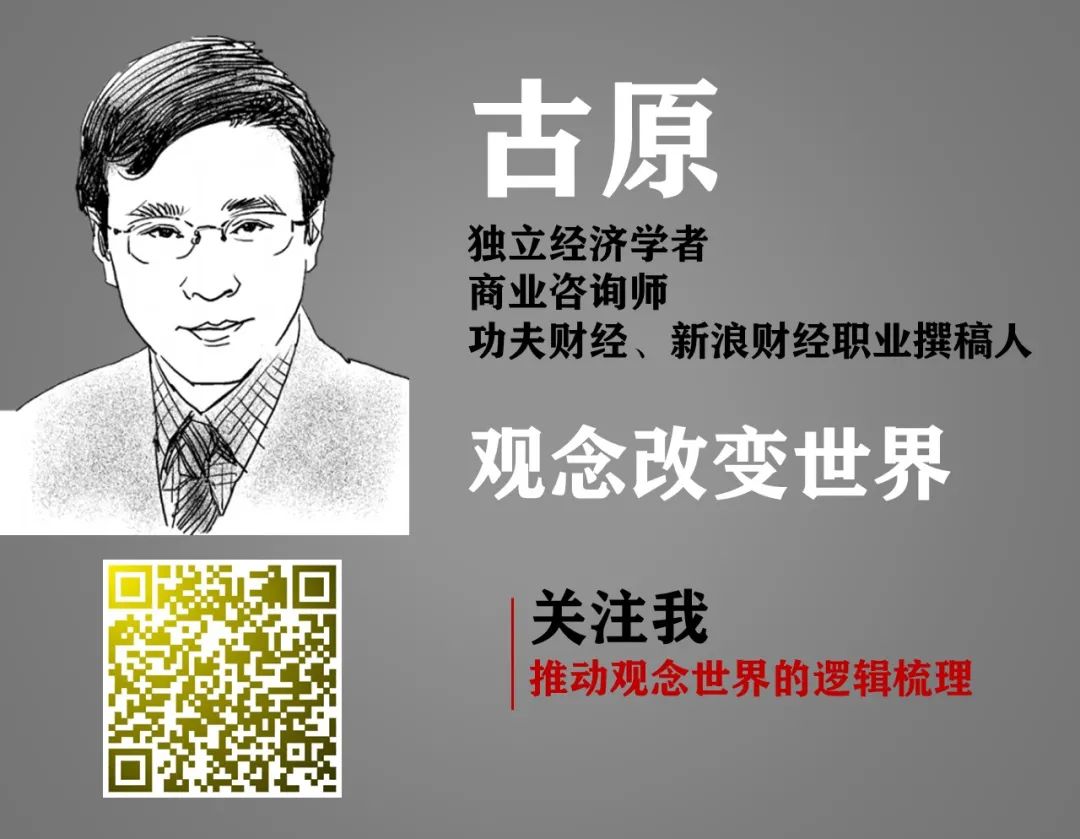
发送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