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划师假扮成神,认为自己可以指挥小民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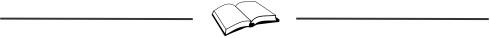
米莱没有否认气候变化。
气候总是在变化。
很久以前,人类就遍布地球。
米莱批评的是气候政策。
它假定人类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
气候灾变论被用于提高气候活动家和气候科学家的补贴,向他们提供资金,和证明国家权力扩张的合理性。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警告人们,不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一些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举措。
换句话说,不要实施那些成本高于可能收益(或可能避免的未来损失)的举措。
此外,未来的损失必须折现到当前。
让诺德豪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古典论点是正确的。
然而,从奥派角度看,它忽略了甚至更根本的问题。
国家当局无法获得关于其气候措施之边际成本与收益的信息。
他们像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策者一样盲目。
他们在浪费资本。
碳排放的好处之一是肥力效应(fertilizer effect)。
空气中更高的二氧化碳集中度会让植物生长得更快。
这个星球正在变绿。
如果气候变化使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绿化并能生产小麦,这也要考虑的效益。
挨饿的人会更少。由于气候变化,一些土地和不动产正在获得价值,而另一些则在损失价值。
彼此如何平衡?
此外,盈亏是在未来发生的,必须在当前折现。
因人为的气候变化而侵犯自由的国家议程缺乏任何经济学基础。
也许人和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们的适应性。
十九世纪末,大街上马粪遍地,科学家们召开了许多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戴维斯[Davids]2004)。
如果经济继续发展,马粪将会淹没道路——于是这种担心也将继续。
这个问题似乎无法解决。
然而,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1886年,格特菲尔德·戴姆勒(Gottfried Daimler)和卡尔·本茨(Carl Benz)同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批汽车。
当汽车开始上路,马粪问题就消失了。
不需要停止发展。繁荣和前所未有的富裕接踵而至。
今天,国家正在限制对内燃机的研究。
从2035年开始,欧盟将禁止销售碳排放车辆。
欧盟计划师想让所有资源都流向电动汽车。
他们擅自假装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技术。
他们认为自己是神,可以指挥我们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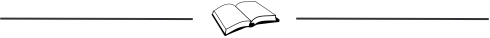
米莱反复强调,国家主义是不道德的。
资本主义是唯有有效率且公正的社会制度。
从像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这样的“奥派”的角度看,效率和道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公正之事不可能没有效率。有效率之事不可能不公正。
另一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正义和效率可以任意组合,例如牺牲一点效率得到更多公正。
像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这样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福利函数,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计算一个社会的整体福利,还可以将再分配考虑进来。
然而,国家主义和国家再分配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而动用暴力总是不公正的。
也许,最人性的品质是创造力。
在自由中,人们创造新事物。国家压制这种自由。
例如,在监狱里,创造性就受到严厉的限制。
德国人必须工作到7月份才能交完他们的税收。他们必须支付罚金。
管制条例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做什么和被允许做什么。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人如果作为企业家获得了成功,那他就是真正的英雄。
因为人们必须将大量精力用于保护自己免受家长式国家及其官僚机制之害。
不允许我们在自由中创造性地工作和行动,是不道德的。
因此,社会主义——更一般地说,国家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悲剧,因为它要对超过1.5亿人死亡负责,也因为从科学角度看,它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因为它是最严重的不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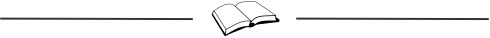
像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和罗马俱乐部这样的怀疑论者(naysayer)预测时没有考虑人的创造力。
从生物角度看,资源有限,细菌、蚊虫或大象数量只能增长到某个限度。
但是,我们人类不是细菌、蚊虫或大象,我们是有创造力的存在。
因此,增长也是没有限度的。
这种反直觉的观点也导致了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imons)与生物学家保罗·欧利希(Paul Ehrlich)之间的著名赌局,后者将细菌、蚊虫和大象的生物学发现推论到人类身上。
欧利希在其1968年的著作《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预测,资源有限的世界中世界人口的增长将造成世界性饥荒。
经济学家西蒙斯是《终极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1981)一书的作者,他认为,人的大脑,也就是人的创造力是终极资源。
如果资源的确是有限的,那么随着资源的消耗和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会变得日益稀缺,且价格将会上涨(剔除通货膨胀)。
1980年西蒙斯向保罗·欧利希提出,选择5种原材料并追踪其价格走势十年以上。
如果这一揽子商品因为变得更加稀缺而价格上涨(剔除通货膨胀),欧利希将赢得赌局,并得到西蒙斯的1000美元。
如果它们的价格下跌则反之。
尽管1989-199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超过100万人,但是这些商品的价格下跌了,西蒙斯赢了。
接着,欧利希就不愿意将赌注提高到10000美元来重复这个赌局了。
静态思维不考虑人的创造力。
它不理解经济上的可用资源如何可能持续增长,而获得这些资源所需的工作时间会持续减少。
这种静态思维不仅罗马俱乐部有,WEF也有,后者旨在作为某种世界政府来探讨世界问题。
由于对人的理性的神化,人们认为这种问题解决方案,正是那些建议成立世界政府的专家和技术主义者的智慧。
人与自然的冲突只是认为制造的诸多冲突之一。
如前所见,柏林墙倒塌后,国家主义者为他们的理念寻找新的支持者(hobbyhorse)。
无产阶级越来越少。由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脱离贫困。
于是,国家主义者和社会工程师们必须寻找新的可以让国家冲过来帮助的受害者。
正如米莱在达沃斯论坛上解释的那样,人为的男女冲突就以这种方式被制造出来的。
但是,在自由市场上没有这类冲突,因为法律面前男女平等。
虽然在市场中性少数群体——即所谓跨性别群体(LGBTQIA+)社群与异性恋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这些群体之间,也被种下了冲突的种子。
尽管如此,平等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声称,他们必须通过再分配让人人平等。
他们主张对他们的静态概念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蛋糕产品”进行再分配,从而助长了冲突。
但是,蛋糕的规模和成分并不是给定的。
在被发现和创造出来之前,准备拿来分配的蛋糕是未知的。
甚至它们的配料也有待发现。
出于这些原因,对奥派经济学家伊兹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来说,一切企业家利润都是公正的。
因为任何人发掘或发现了新事物,都应允许其拥有之。
发现者就是拥有者,这是公正的。
剥夺发现者的社会必定要放弃技术进步和财富创造。
蛋糕会变得更小,更不好吃。
西班牙最有钱的人,“飒拉(Zara)”的创始人阿曼西奥·奥特加(Armancio Ortega)估计拥有800亿欧元的财富。
如果剥夺他的财产,将它们平均分配给世界上80亿人,地球上每个人能分到10欧元。
一顿麦当劳之后,一切都化为乌有。
同时,飒拉的母公司Inditex名下的所有工厂、员工和它所满足的千百万顾客,将成为历史。
奥地利学派教导,为了脱离贫困,储蓄者,也被称为资本家,必须受到善待。
储蓄使资本品的创造成为可能,而资本品,例如机器、计算机或软件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而因为工资取决于工人生产了什么,更多的储蓄和资本品意味着更高的真实工资。
一位美国农民赚的钱是印度农民的100倍,是因为前者的生产力高100倍;而他有高100倍的生产力,是他的资本品是后者的100倍。
由于有了拖拉机、GPS、灌溉系统、计算机和肥料,美国农民一天的产量是只有牛拉犁的印度农民的100倍。
对利润和资本征税是最有害的税收。
嫉妒导致了对利润和资本的征税,它伤害了赚得最少的,最脆弱的人,因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下降了。
人们经常被煽动家欺骗,看不到其中的联系。
哈维尔·米莱成功地打破了这种欺骗。这是他的伟大成就。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