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本位向法币本位的转变,是货币制度的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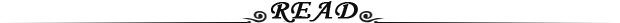

在本文中,我将延续米塞斯、罗斯巴德和萨勒诺的传统,探讨健全货币制度对货币质量的影响。
货币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类似,取决于使用者对其效用或品质的认可。
货币质量可以定义为“行动人感知到的货币履行其主要职能——即充当交换媒介、财富储藏手段和会计单位——的能力”(巴格斯,2009年,第22-23页)。
货币质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其购买力。而货币制度的质量,则是指一种货币体系成为优质交换媒介、财富储藏手段和会计单位所提供的制度框架的能力。
尽管货币体系或制度的质量是由行动人主观感知的,但存在若干客观特征往往会左右这种感知。
在试错过程中,行动人通常不会将对制度框架的认知建立在反复无常的臆想之上,因为误判的后果将由他们承担。
在货币体系客观特质的引导下,参与者往往能通过对冲贬值风险或从货币升值中获益,从而更有效地守护其货币财富。
本文将对"优质"货币体系的这些客观特质进行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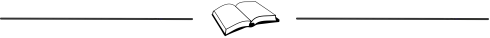
货币体系的质量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始终未得到足够重视。
从制度视角对货币体系进行的比较分析研究寥寥无几。
教科书也鲜少深入探讨货币体系的特质,怀特(1999)的研究是个例外。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现行法定货币体系框架下的货币政策分析,有时会辅以某些历史上的货币制度演变的叙述,却未提供系统性比较。
这种比较研究的缺失或许源于这样一种认知——人们认为现行货币体系已臻完善。
由中央银行掌控的法定货币体系可通过调控手段,创造出理论上能完美履行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会计单位职能的货币。
此外,货币制度的特质难以量化,也无法直接应用于计量经济学分析,这使得该议题对现代计量研究缺乏吸引力。
然而近期金融危机引发了对金融体系(尤其是货币体系)架构的质疑,这使得货币体系的比较分析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货币体系的质量影响着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的购买力。
尽管人们普遍关注货币数量及其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但货币质量与货币体系的质量对货币价格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
实际上,货币数量可被理解为决定货币质量的若干特征之一,而货币制度增减货币数量的可能性与能力,正是衡量该货币制度质量的重要特征之一。
货币体系的变革可能导致货币质量与购买力的骤变。
更具体而言,货币制度的更迭会引发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价值的显著变化。
设想行动人认为新货币体系在交易媒介、财富储存和会计单位方面的功能均逊色于旧体系,这将导致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估值程度降低。
这种变化可通过个体在制度变迁前后价值尺度的具体案例加以阐明。
货币制度更迭前的价值排序表 | |
20th | 第五个10美元 |
21st | 汉堡套餐 |
22nd | 第六个10美元 |
23rd | 芝士汉堡 |
24th | 第七个10美元 |
25th | 一瓶红葡萄酒 |
26th | 一瓶白葡萄酒 |
在我们的示例中,一个人口袋里有7张10美元纸币,他却不会购买标价为10美元的葡萄酒。
然而,如果他认为一个芝士汉堡的价值高于他所拥有的第7张10美元纸币,他就会掏出一张10美元纸币去购买这个芝士汉堡。
同样,他也会用第6张10美元纸币去购买一份在他看来价值更高的汉堡套餐。
让我们探讨一下货币制度变革后的价值排序情况——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货币的质量有所下降。
在行动人眼中,新的货币制度在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储存和会计单位的功能上,表现远不如之前的制度。
货币制度更迭后的价值排序表 | |
20th | 汉堡套餐 |
21st | 芝士汉堡汉堡套餐 |
22nd | 一瓶红葡萄酒 |
23rd | 第五个10美元 |
24th | 一瓶白葡萄酒 |
25th | 第六个10美元 |
26th | 第七个10美元 |
我们注意到,如今商品在价值层级中的排序相较于货币单位而言,比以往有所提升。
制度变化后,此人愿意花费10美元购买一瓶白葡萄酒。
同样,她也会用10美元去购买红葡萄酒、芝士汉堡或汉堡套餐。
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会随之上涨。在货币数量未增的情况下,由于货币制度质量下降,货币相对于商品的价值降低,从而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
购买力的急剧变化可能正是由货币制度的变更所引发。这促使我们有理由深入分析不同货币制度的质量,以及制度变更对其质量的具体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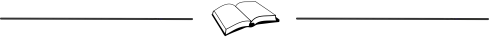
货币制度为货币履行其职能提供了框架。由于几乎所有货币体系都能同样良好地履行会计单位功能,且该功能仅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受损,我们将重点关注优质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手段的特征。
我们将从优质交换媒介的特性及货币制度对其影响展开论述。优质交换媒介需具备低储存与运输成本,其他特性还包括易操作、耐用性、可分割性、抗腐蚀性、均质性以及易识别性。
在当今纸币信用本位制下,由于货币单位的物理适用性和供给成本已大幅降低,这些特性基本保持不变。
但在商品货币本位制下,当社会从一种商品货币转向另一种商品货币时,这些品质可能发生变化。
例如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可能提升货币品质,因为黄金比易氧化的白银更具耐久性。交换媒介更关键的属性在于使用者数量。
更多使用者意味着对交换媒介的需求增加,当更多人在贸易中接受该媒介时,其效用也随之提升。货币体系的变革可能扩大使用者群体,从而提升货币质量。
例如十九世纪末,越来越多国家放弃银本位转向金本位,黄金作为货币的广泛使用提升了其货币品质。
同理,从德国马克转向更广泛流通的欧元,或从国家信用货币转向全球信用货币,都能增强交换媒介的货币品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交换媒介品质的提升趋势可能被其价值储藏功能的弱化所抵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交换媒介最重要的特征或许在于该货币作为消费品或生产要素存在大量非货币需求。
这种基于其他非货币目的的需求,确保了存在强烈且持久的未被满足的欲望(门格尔1892年著作第5页)。
非货币需求如同货币持有者的"保险单",因其稳定需求而维护了货币价值。即便在最坏情况下——当政府废除该货币法定地位,或人们转而采用其他交换媒介时——具有非货币需求的货币依然能保有使用价值。
反之,非货币需求极低或缺失的货币一旦被废止货币地位,其价值将几近归零。这类货币的价值完全依赖于货币性需求及市场信心,其价值波动性远高于具有稳定非货币需求的货币。
当这种"保险机制"失效时,即便货币供应量未发生任何(预期)变化,货币品质也会恶化,导致其购买力呈下降趋势。
原因在于:对缺乏非货币需求保障的货币持有者而言,货币废止与价值彻底丧失的风险,远大于具有使用价值的货币单位。
缺失这种保障机制时,货币需求往往衰减,继而引发购买力下降。
因此,当货币制度从具有充足非货币需求的体系(如金本位)转向缺乏相关非货币需求的体系(如法定货币本位)时,无论(预期)数量如何变化,货币制度的质量都将实质性地降低。
价值储存功能是货币的另一项重要职能。良好的财富储存手段具有若干特征。
货币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其数量具有可增长性。不同货币制度通过不同机制实现货币量增长,从而影响货币质量。
因此,货币体系可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设定严格程度不等的限制。当货币体系从严格限制货币量及其可能增长的制度,转向更易实现且更难预测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制度时,即意味着货币质量的恶化。
货币制度的质量与其孕育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样重要。某些货币制度比其他制度更易引发商业周期、过度负债和流动性枯竭问题。
商业周期波动、过度负债与流动性危机可能导致政府或货币当局实施干预与救助措施。
这些救助行动往往伴随着货币数量的扩张,甚至可能导致货币体系质量被稀释——例如暂停铸币兑付,或建立新的货币秩序(如引入全球法定货币)。
因此,当货币体系向更不稳定的方向转变时,货币质量将受到负面影响。
非货币化的可能性是影响货币质量的一个相关因素。有些货币体系比其他体系更容易出现非货币化情况。若货币体系伴随着不稳定的金融部门,可能会引发金融崩溃或政府救助,而这会危及人们对货币单位的信心。
另一个影响货币作为价值储存手段的因素是政府可能采取的普遍干预措施。政府干预往往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或削弱储备支持,以牺牲货币质量为代价来维护自身利益。
例如,政府可能没收其法定货币的黄金储备以支付开支,从而降低货币质量。相较于那些政府拥有更强控制力的货币体系,有些体系更不容易受到政府干预。
货币制度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越强,货币质量就越高。若转向一个对政府干预依赖性更强或更易受政府干预的货币体系,则意味着货币质量的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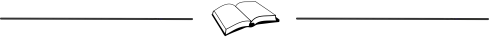
我将分析不同货币体系下的货币质量。 首先从最高质量的货币体系开始,逐步向下探讨质量较低的体系。在百分百金本位制下,只有黄金(或百分百黄金背书的凭证)是货币,以及银行对其持有百分百准备金的活期存款。
以下分析在做相应调整后,也适用于其他100%商品本位制,例如100%银本位制。我选择黄金作为例子有两个原因:金本位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及其独特属性。
百分百自由金本位制具备优质货币的所有特质。黄金具有体积小而价值高的特点,从而降低了储存和运输成本。
它在交易中易于流通且可分割性强,质地均匀统一,成色易于辨识且抗腐蚀性强。全球范围内对黄金存在巨大的非货币需求。黄金还具有较强的囤积属性,能够进行大宗买卖而不产生损耗。
此外,黄金的生产成本极其高昂,现存黄金储备量也极为庞大。任何人都可以铸造金币——政府在货币体系中并无特权立足点。因此,政府很难操纵黄金体系。
唯有通过直接削减铸币成色或改变货币制度本身,政府才能干预黄金价值。更何况,这两种黄金操纵手段可能遭遇强烈抵制,因为当黄金掌握在民众手中时,这类操作将暴露无遗。
此外,在百分百金本位制下,存在无限且无条件的兑现机制。从定义上看,银行体系具备完全流动性;由于拥有百分百的储备金,挤兑现象无法撼动该体系。
与其他货币制度相比,这种体系下经济和政府对货币质量的负面影响显著较小。究其原因,百分百金本位制不仅能增强经济韧性,还能有效限制政府支出。
由于制度设计上杜绝了信贷扩张和人为压低利率的做法,因此不会引发信贷驱动的经济周期。
此外,征税措施不得民心,政府债务无法通过货币化手段解决,必须依靠税收来偿还,这迫使政府必须保持更为审慎的财政纪律。
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黄金产量增速时,该体系内会呈现缓慢的物价下行趋势,进而降低举债的吸引力。因此,过度负债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在完全自由的百分百金本位制度下,货币竞争同样存在。黄金并非被强制作为货币使用,其他货币形式可与之自由竞争。
货币生产领域的竞争确保了货币质量——劣币会被良币驱逐出市场(哈耶克,1978年,第1-3页)。
唯有最能持续发挥会计单位、财富储存和交易媒介功能的货币才能在自由竞争中胜出。
这种体系不存在中央银行、货币垄断或法定货币法,因而将形成最佳货币的发现机制。
不同发行者通过试错过程竞相向客户提供货币,低效的货币生产者终将淘汰,只有那些在数量与质量上最契合消费者需求的高效货币生产者才能存续。
鉴于货币使用者通常偏好稳定币值,市场竞争将推动货币体系向稳定性方向发展。
最后,这种货币体系通常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
活期存款100%的准备金要求,有效避免了银行挤兑演变为全面的银行业危机。此外,对于其他类型的期限错配(即短借长贷),也存在严格的限制(Bagus 2010;Bagus和Howden 2010)。
短借长贷是一项风险极高的业务——竞争对手可能通过持有短期债务并拒绝展期,迫使银行破产;投机者也可能通过做空银行股,试图引发针对银行短期负债的挤兑。
客户自然倾向于选择那些限制此类高风险操作的银行。
简言之,在自由市场中,期限错配受到严格约束,银行系统性地误判短期可再生储蓄规模的可能性极低。
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能够展期短期债务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通过持续信贷扩张来增加货币供应以缓解短期债务展期压力的机制,那些助长过度期限错配的因素(如政府对银行的担保)将受到制约甚至消失。
因此,在百分百金本位制下,金融体系展现出高度稳定性,政府通过稀释货币价值或改变货币制度来救助金融体系的动机也将大幅减弱。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