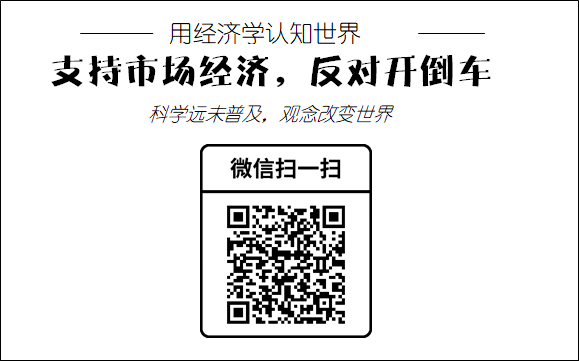历史上,市场化改革的三次大争论!那些破坏改革的罪人是谁?
熟悉中国当代史的朋友都知道,改革开放来之不易。
自邓公开启市场化改革起始,反对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整个改革开放,就是观念的斗争史。
看过往的历史,我们不能只看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我们更应该看观念史。就是哪些具体的观念在影响着历史,在推动着历史发生变化。
江泽民的功劳
历史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哈耶克说:是由社会大多数人的观念决定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由那些传播观念的人决定的。
那么观念是什么呢?观念是事物的因果关系。
计划经济,这四个字不仅仅是一个词,背后是有一套因果关系的,倡导计划经济是在说计划方式(即政府指令生产)也可以发展经济。
语言不仅传播智慧,而且传播难以消除的愚昧。
一套特定的词汇本身的局限性及它所具有的含义,有时就决定了具体的观念,也决定了社会现状。
计划经济这个词汇以及附着于其中的理论,如果名词没有被摒弃,那人们就需要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进行表达,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
这些数十年来构成的传统词汇,以及根植于这套词汇中的理论和解释,往往会让我们误入歧途。
从一个人说话,就可以看出,他思维的根基来自于哪些理论。
四十多年前,以下这些词汇构成了知识分子主流的观念:
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实践、异化、基础结构、上层建筑、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
离开这些词,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如何描述社会、解释社会。
我们站在四十年后,我们已经很少在舆论中看到上述词汇了,因为计划经济及其附着的错误理论,已经在慢慢失势。
江泽民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正式将计划经济这个词排除在核心舆论中,在舆论环境中,宣布了计划经济这一名词已不再政治正确。
这看起来,只是换了一个说法,但却让附着在计划经济这个名词上的全套观念体系逐步衰弱。因为失去了固有的名词,这一类型的观念将无法展开论述。
邓小平的论述一直是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列论述,而江泽民则开创性地摒弃了计划经济这一名词,邓江二人合作,在观念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自此,建立在计划经济这一名词上的那一套话术体系就逐步在舆论上消亡了。
观念的斗争,就是围绕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词汇展开的,邓小平与江泽民通过观念的修正,在第一次大大规模反改革的舆论浪潮中,帮助改革派赢得了胜利,为今天中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反市场化改革的舆论潮一共有三次,也许通过回顾这个历史,会让我们看清市场化改革所遭遇的艰辛。
第一次大争论
在第一次大争论前,其实也有一些小争论,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了小范围的争论。
1982年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薛暮桥、吴敬琏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时间点,理论界是有一些争论的。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邓的评价,平息了争论。
真正的大争论,是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这是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提法在风波后遭到了有些人的批判,认为“市场化、私有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
这次大争论,以皇甫平系列文章为重要起点。
皇甫平真名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支持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
“皇甫平”系列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大家知道,此前几年,东欧发生剧变。
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
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
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
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
有人气势汹汹地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
1991年4月,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后,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
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
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
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在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
批判到了高潮点。
9月1日,江泽民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却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的鲜明态度。
邓小平在1992年启动了南巡讲话,就是针对这一次舆论对改革开放的批评风潮。
之所以南巡被评为二次改革开放,原因就在于此。
南巡讲话,邓小平成功地说服了更大范围的民众支持改革开放,并压住了这一股质疑改革开放,讨论姓社姓资的舆论。
南巡讲话后,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正是邓小平以他自己的独特地位和出色的传播能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出台,创造了好的舆论环境。
这一次的反改革的思潮中,受到计划经济思想影响的主流媒体中的从业者们是主要的参与者,是主要由主流媒体发动的。
而第二次反改革的思想风潮,就换人了。
第二次大争论
2004年开始,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开始出现了又一次的反改革的大争论。
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大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
这一次的旗手,至今活跃在中国舆论当中,那就是著名的郎旋风。
郎咸平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一文,一时间国内外互联网纷纷转载,被称为又一次“郎旋风”。这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一次挑起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
“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惟一导向、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
而文章标题就鲜明界定今日中国是“人吃人的中国”了!
郎咸平系统地通过否定国企、医疗、教育、住房、农村、司法等改革来全面否定改革开放。
最后的结论是改革开放造成了五千年仅见的“人吃人的中国”?“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年来所仅见。”
郎咸平更是借着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攻击国有企业改革,一下成为了中国的顶级网红砖家。
他的主要观点有三:
(1)国有制是一个好的制度,不需要改革,只要建立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制度;
(2)国企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以出卖全体人民利益为代价;
(3)国资流失到私人企业手中,造成今日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严重不公。
郎成平是从根本上否定国企改革。郎成平在台湾出生,在美国留学,在香港任教,他如此厚爱国企,为何不在台湾、美国和香港鼓吹呢?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格林柯尔公司董事长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
对此,顾雏军指责郎咸平“诽谤”,并对其提起诉讼。
这就是著名的“郎顾之争”,这场争论最后在郎大胜、顾锒铛入狱为结局。
他发表言论时正好是“2005年为改革年”“国企改革攻坚战”时刻,郎的言论符合了某些“左”派人士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心态,他们纷纷著文呼应,在中国报刊传媒制造了一场“郎旋风”,不仅报刊传媒上宣传“郎旋风”,多家知名出版社出版《郎旋风》为主题的书籍,并有著名“左派”人士写序吹捧。
甚至有人吹捧郎是中国惟一有公信度的经济学家。
更奇怪的是郎成平侮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人吃人的中国”,一向自诩“社会主义卫士”的“左”派却缄口不言。
各路左派人士纷纷登场,认为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后造成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背离了社会主义,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广大工农再一次成为被剥削的“弱势群体”。
基尼系数不仅超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已经达到0.45,突破警戒线,贫富矛盾已达到一触即发之势,等等。
一些自许为“非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有的甚至采取了发表“声明”这种学界少见的形式。
另一方面,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不少人,如赵晓、张文魁、张维迎、张军与汪康懋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
北京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的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以及据说是这种经济学主导下的国企改革的场所。
郎咸平明确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自称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
而在几个月前,郎咸平还著文欢呼“民营企业的春天”。
郎咸平在这一阶段的所谓反转,其实是看到了中国舆论中反改革开放的苗头,他改变立场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中国舆论市场获得站位拿到掌声。
当然,他是成功的。
郎咸平成功地在中国舆论场上位,成为红极一时的网红经济学家,捞金无数。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文件内容共36条,简称为“非公36条”。
这是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文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
“非公36条”颁布后,2005年4月20日,由105位人士署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标题是《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被称为是左派的“新万言书”。
他们认为“非公36条”“违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违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引起社会动荡”。
除了郎感平,另一位所谓“右派”的代表人物秦晖,则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了这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争论。
这次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的另一个特点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联合,是“左”派与海外所谓右派(实际仍是左派)大联合。
血汗工厂论,中国发展是建立在破坏环境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只肥了腐败的官员等等舆论成为民间的主力舆论。
秦晖作为中国著名的意见领袖,在这次思想辩论中,站在了改革开放的对立面。
秦晖搞出来一个新理论,叫低人权优势,他还是血汗工厂的概念提出者。
以四十年观念史的发展来说,秦晖是中国最坏的理论恶人,因为这两个概念至今流毒甚广。
如前文所述,提出概念,理论,并能影响他人的,即是观念传播者。
秦晖和郎咸平看起来是两派,但其实是同一派。
二者几乎在同一阶段,对改革开放发起了质疑。
低人权优势、和血汗工厂论,完全否定了中国引进外资,让农民走进工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
秦晖同时,也是当时国企改革的反对者。
他主张“只分不卖”、“民主先行”,将国企改革与政治体制关联起来,同时用“尺蠖效应”这种概念认定当时的改革开放和国企改革,只肥了少数人,而受损的是大部分人。
这在当时,迎合了国企下岗工人强烈的不满情绪。
秦晖和郎咸平二人,成为了当时反改革的两大意见领袖。并再一次成功地挑起来姓资、姓社的大讨论。
本质上来说,今天的各种舆论乱象,就来源于这一次的思潮。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当时的国企改革碰到了巨大的问题。
不仅各地国企职工下岗引发各种群体事件,并在2009年酿成了著名的通钢事件,工人为了反国企改制,将已完成收购手续的民企职业经理人打死。
东北的国企改革步伐因此改变。从原来的大力推进,变成了谨慎处理。
东北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工业发展之地,但却未能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重放光芒,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市场化往前推进受到了舆论的反击。
郎秦二人,作为观念传播者,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大的罪人之一。而其中,秦晖作恶基于郎咸平,因为秦晖更有理论和概念创造的能力。
他的血汗工厂论、低人权优势等理论,构建了另一套话术体系,这套话术体系至今依然是中国反市场舆论力量的主流话术体系。
胡锦涛作为当时的主政者,提出不折腾,其实是回应这一股反改革开放的舆论,意思是不再折腾姓社姓资的问题,坚定地搞改革开放。
2006年的“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并谈到20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几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吹响了新的号角,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新的征程。
但客观地说,郎秦二人已经将观念的种子种下,二人对改革开放的批评,至今依然构成了反对改革开放的舆论阻力和主要理论。
今天中国舆论中,各种反市场、反改革的声音不过是郎秦二人信徒的鹦鹉学舌罢了,没有任何新意。
那么第三次的争论在哪里呢?
第三次大争论
严格说来,第二次大争论持续的时间很长,可以说他一直持续到现在。
虽然站到台前来的人物不停地换人,但舆论场中的核心观念和思想与第二次大争论没有什么两样。
但依然存在第三次大争论。
这次争论的主角,叫司马南。
与第一次,第二次不同的是,前两次质疑改革开放的人是主流媒体中的编辑和学术界的教授,而司马南则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网络混子。
因为2021年,中国已来到了互联网自媒体时代。
在这个时代,专家们早已走下神坛,郎咸平也已失去光环,更加民粹更有煽动力的意见领袖出现了,司马南正是第三次大争论的核心人物,并且是唯一的意见领袖。
大争论的起手式,依然是质疑国企改革。
联想事件成为抓手,司马南仅仅根据一个自媒体上的文章,就搞出来了九问联想,一下引爆舆论。
与前几次大争论主流媒体参与不同的时,这一次主流媒体全部作壁上观。
司马南成功在全网吸粉五千万,聚集到各种反改革开放的舆论声音,即使是一直讨厌司马南的秦晖粉,虽然痛骂司马南,但并不认为司马南在联想事件中的质疑有什么问题。甚至他们有相同的主张,比如都主张免费医疗
司马南的主题非常明确,不管任何事件,他必搭上资本。
他已然嗅到,反资本的民间舆论越来越强大,而这本来就他长期的主张。
每一句话,每一次评论,都指向资本,暗指背后的官商勾结。
而与之呼应的是知乎、B站等年轻人聚集的平台,出现了大量反资本的声音,甚至挂路灯的声音都不绝于耳。
这些反资本的声音,也不是无端来的,而是民间不少思想社团积极传播某些理论的结果。如果你认真观察,你会发现,这些挂路灯的声音背后对应着一整套四十年前的话术体系。
在中国主流舆论界不再出现的这些话术体系又来了。
司马南虽然不敢直接使用这些话术体系,但他精于观察舆论风向,抽取了不同的反市场化观点中的共识,最后聚焦在资本这一主题上。
这是区别于前两次争论的重大区别。
前两次争论,还是舆论界、学术界在主流媒体上展开的大讨论,而这一次则是在更加多元的网络自媒体上呈现的。
前两次参与的主要是社会精英层,而在这一次声浪中,主流媒体已经消失,网络舆论占据了主流。
尽管有些自媒体大V没有参与,但是他们共同营造了这一次大争论的舆论氛围。卢克文、周小平,远方青木等新一代的网络舆论领袖,都为司马南的成功上位提供了受众。
前两次尚有两派大V争论,但这一次,司马南一人挑战无数小小小咖,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份量的对手。
这些民间舆论和一些社会政策,再一次引发民间对开倒车,否定改革开放的担心。
对此,高层的表态是: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结语
改革开放一定会带来问题,当他带来问题时,人们的反思往往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改革开放错了导致的,第二个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不够导致的。
但如何去理解这些问题,他们需要观念体系、话术体系。
比如,四十年前,中国其实是一个福利社会,国企有高福利,企业办食堂、澡堂、托儿所、学校甚至医院,从生到死全包。而人民公社时期,也搞过九包、十包类的全民福利,最高峰时吃饭都包了。
可是,鲜有人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福利社会,以至于一部分人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时候却肯定欧洲的高福利社会。
失去了对社会现象精准的、达成共识的定义和概念,就必然导致观念的混乱。
应该说,在很长时间内,官僚体系对市场的认知比民间舆论更为清醒,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九十年代启动的国企改革,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处理已破产的国企,因为当时大量的国企已无法进行实质经营,只能依靠政府指令贷款续命。
光四大行上市前,剥离的不良贷款就是天文数字,这些不良贷款很多都来源于对亏损国企的补贴。
是否能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是在市场化改革中遇到的难题,这一难题的本质是观念上的痛苦,当市场化某一领域时,人们在短期内并未感受到市场化带来的变化,于是就开始在观念上反对。
医疗改革就是如此,人们主观上认为医疗是失败的改革,但实际上,哪怕只是让医疗体系市场化程度高一点点,中国医疗服务的性价比和服务能力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
然而,普遍的观念却不支持这一认知,这一观念是今天医疗进一步市场化无法推进的根本阻力来源。
很显然,在很多领域 ,市场化不够,法治不够,产权保护不够这些问题才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无可质疑。数十年来流传的崩溃论已然破产。
贫富差距论、基尼系数论,也已经破产,因为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农村人买车都成普遍的行为。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难点,依然集中在少数问题上,也即这些反改革舆论重点攻击的要点上。
教育、医疗、环境、国企、劳资等问题,依然是改革难点中的重灾区。
而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点,因为全世界的主流观念依然不支持这些领域的市场化,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世界的各种观念构成了对中国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想要超过其他地区,缺乏观念支持。
有些更为市场化的领域,比如劳动力市场,反而被批评为落后的制度。
不少“文明人”以欧美为标榜,要将那些地区的所有反市场的政策一股脑打包回中国,包括教育、医疗、福利制度、劳工保护等等。
他们并不能观察到,第三世界很多国家无法完成工业化,就是因为他们复制了上述反市场的制度。
我们或许可以不需要盯着政府在干什么,我们只需要盯着舆论的主要风向。政府其实是大多数民意的投射。
如果你要说中国政府数十年来改革的力度,市场化的勇气,我并不认为没有。
在1992年,国务院就颁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要将教育医疗等事业单位定性为产业。
这在很多欧美发达国家,都没有这么定义,在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医疗都是公办的政府运营模式,他是公共服务,不是产业,并不以利润为目标。
但是,这一定义,被民间舆论怼回来了。自这一年起,所谓左右两派都在疯狂咒骂这一政策,直至现在,你依然会发现,这是主流的社会观念。
普遍的群体观念,决定着社会的进程,也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未来。
政治人物、思想者、专家教授、舆论记者评论员,甚至自媒体达人,他们都是舆论中的影响者,他们在主导观念的传播,而最终,政府的行动必然要符合主流人群的观念,否则无法推进具体的政策。
很多人并不能意识到,观念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驱动力,他们把各种政策神秘化,归因于不可知不可捉摸的人的内心。他们认为政治人物无所不能,夸大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
甚至将这些反市场言论归结于言论自由,为什么不可以说?也有人将这些认定为思想市场,认为这是思想的自由市场。
思想不是市场,他无法交换。谁的理念能胜出,是没有规律的。有时,往往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元素,比如观念传播者的地位,比如他们的技巧。
司马南以胡同大爷的身份出场,就是很高明的民粹传播技巧。
从观念传播的角度来说,批评政府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其实你会发现,绝大部分政府的政策,都是过往的舆论观念斗争的结果。
政治和政治人物都必须向观念斗争的结果——大多数人的观念妥协。
你能打败司马南,能说服司马粉粉转黑,才有可能改变社会。
因为,影响社会进程的,正是各种观念的斗争。
你预测未来,也不需要用各种阴谋论来解读,而只需要回到社会舆论层面,你就能观察到趋势。
只有观念可以改变观念!市场经济的观念传播,任重而道远。
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未能得以传播,就是正确的社会科学未能普及,那么,愚昧就将主导社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