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因何而愤怒?他们真的是在追求公平吗?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

“小镇做题家”因何而愤怒?他们真的是在追求公平吗?

文/乌里单刀
近日,某明星考上了国家话剧院引发了热议。
针对部分网友的议论,《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又为什么要考编》,力挺易烊千玺。
文章说:
考编的普通人大有人在,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
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
但这是一种幻觉,似乎认为自己的收入低,是因为明星从既定的盘子里抢走了自己那一份。
由于文章使用了“小镇做题家”这个明显贬义的名词,因此迅速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这已经是“小镇做题家”的第二次“爆红”了,而上一次“爆红”是在2020年。
2020年11月,藏族小伙丁真,因为“一脸纯真朴素的笑容”而走红网络,成为“新晋顶流”。
走红后的丁真,被当地旅游部门聘为成为旅游大使,得到了麻瓜梦寐以求,却求而不得的编制。
和易烊千玺考上国家话剧院一样,这事也引发了一批网民的质疑。
有人直接质疑,当地有关部门对丁真的招聘是否公平、合理,有没有按照国企员工的招聘标准来。
更有人忿忿不平:我明明学历比丁真高多了,想考个国企还考不上,他凭什么?
巧的是当时,另一个官媒,《中国青年报》下属的《中青评论》发表了《“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同样地力挺丁真。
文章说:
尽管英俊的面孔、独特的文化背景、在艰苦环境下独立生活的经历,都对他的成功有所作用,但“缺少学历”这个特征,还是深深扎到了那些失意“做题家”们的心。
倘若一个“做题家”的生活基本令人满意,足以回报其求学生涯中付出的努力,他根本就不会去在乎这位康巴小伙是否幸运,以及他又是靠着什么才得到了这种幸运。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努力未能给他相应的回报,使其总有一种被剥夺感,“丁真们”都可能令其芒刺在背,痛彻心扉。
和《中国新闻周刊》一样,由于使用了“做题家”这一带有嘲讽意义的词,《中青评论》甚至《中国青年报》也受到了网民的“炮轰”。
有意思的是,“小镇做题家”原本是一些人的自嘲,所以有人把“小镇做题家”的污名化算在了《中青评论》和《中国新闻周刊》的头上。
“小镇做题家”一词,源于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的网友发帖,豆瓣用户“水果糖”在小组总结称,“小镇做题家指的是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他们曾凭借刷题和超强的应试能力,经过高考的角逐从小城镇考入一流高校,以为能从此平步青云,但进入大学后却发现,自己曾因成绩优异而拥有的光环逐步瓦解,特别是与来自大城市的同学相比,在思维、眼界、家境、 社交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脱离了做题模式后,他们对新环境无所适从,甚至自我设限,以致在升学或求职过程中处处碰壁、屡屡受挫,陷入自我怀疑的焦虑迷茫情绪。
“小镇做题家”的帖子引起了组内热议,大家分享自己相似的失意经历,在自嘲为“废物”中寻求共鸣,于是,“小镇做题家”就成了部分 211、985高校毕业生自我调侃的标签。
事实的确是这样,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人与来自大城市的人相比,确实普遍地在思维、眼界、家境、 社交能力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只要诚实地面对内心,恐怕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不过,虽说敢于自嘲的人内心是比较强大的,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人都能接受得了这种自嘲。
比如有人说,我自嘲可以,但你不能用来嘲讽我,否则就是对我的冒犯,就像有人用犬子、贱内来谦称自己的儿子和老婆,其他人却万万不可把他的儿子和老婆叫做狗仔和贱人。
对“小镇做题家”的嘲讽刺痛了人们的心,激发了众怒,和这个群体的数量庞大有着莫大的关系。
几十年的城市化发展,无数来自农村与小城镇的人涌进大城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通过考进当地大学,毕业后留在本地的。
对这部分人来说,“做题”是他们阶层上升的成功路径,对“做题”的嘲讽无疑就是对他们的否定,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会反感这样的嘲讽。
他们认为对“小镇做题家”的嘲讽是“何不食肉糜”,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冷嘲热讽这种东西,只要你不在意就伤害不了你,尤其是如果你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的话,你会在意那些无聊的嘲讽吗?
你只会轻蔑地骂他无知和傻逼,然后该干嘛干嘛,不会在这种事情上纠结哪怕一分钟。
只有日子过得不那么如意的人,才更容易为“小镇做题家”对号入座,愤怒不已:
“做题家”怎么了?“知识改变命运”,高考改变人生,不也是当年全中国上下都公认的社会教育、就业资源分配方式吗?
这句愤怒的反问,充分暴露了(某些)“小镇做题家”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公平。
政治的肮脏之处就在于,99.99%的人总是企图用政治手段去分(掠)配(夺)社会资源(实则民众创造的财富)。
是的,对某些人来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年代,只要你考上了大学甚至中专,国家就会给你分配工作,这些工作岗位要么在机关单位,要么在国企,总之都是国字头的铁饭碗。
对许多人来说,国字头代表着“公共资源”,公共的资源当然是人人有份,当然要公平分配。
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追求成为食税阶层中的一员,他们渴望的铁饭碗是用权力和垄断打造的。
对这样的“小镇做题家”,有位朋友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中国人读书自古都是为了编制,毕竟学而优则仕嘛。
另一位朋友说,读书人不在编,是对读书人最大的伤害。
自从有了科举以来,世世代代,读书人都是在编的,现在(一大部分就业岗位)归资本家掌控了,适应不了。
“小镇做题家”真正的问题不是高分低能,而是痛恨家族积累,痛恨财产继承,痛恨读书人没了地位,痛恨资本家横行。
“小镇做题家”的观念底色是客观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他们觉得,只要自己付出了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努力,那就必须得到他们想要的收获。
所以他们嫉妒没有学历却能名利双收的网红和明星,为做导弹的收入比不上卖茶叶蛋的而愤愤不平。
殊不知价值是主观的,所有在市场上谋生的人,都必须接受消费者的评判,只有消费者认为你的服务有价值,才会把选票(即钞票)投给你,这就叫市场的民主。
市场不会看你曾经读书有多努力,考试成绩有多好而给你回报,而是看你服务了多少消费者,是否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网红和明星,不管是凭借漂亮的外貌,还是凭借说学逗唱或插科打诨的才艺,他们都肯定满足了人们的某些需求,所以才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这才是他们能够名利双收的真正原因。
请问,这有什么不公平的?怎么在这里就不讲民主了?
有编制的人,并不需要把服务消费者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的工资并不直接来自消费者的投票,而是来自公共财政,也就是税收。
税收是强制的,所以不管消费者满不满意,都要被迫掏钱养活有编制的人。
因此,渴望编制、希望国家分配工作的“小镇做题家”,有什么脸面向社会要公平,这种公平对被迫掏钱的人公平吗?
“小镇做题家”反市场,痛恨资本家,痛斥996,所以向往有编制的朝九晚五和双休日,以及各种法定节假日,但这些几乎是编制独有的福利待遇,本质上都是强迫纳税人负担的,你们怎么就不为纳税人呼吁公平呢?
改革开放前,来自农村与小城镇的人,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考,毕业后由国家收编进体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改革开放后,人们才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这么说,市场经济给人们搭起了无数座通往幸福生活的大桥,人们再也不需要死抱着编制不放了。
甚至,很多人主动放弃了编制,选择了下海创业,在市场中摸爬滚打,通过服务消费者而不是服务领导来赚取财富。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考编考公务员,那就说明市场受到的管制越来越多,人们出人头地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才会更加渴望进入体制捧铁饭碗。
因此反市场的言论和行为,实则就是在堵塞自己和别人的出路,摧毁那一座座通往幸福生活的大桥,然后一步步退回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老路上。
“小镇做题家”痛恨家族积累,痛恨财产继承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小镇做题家”只要好好想想,观察观察自己身边的人和家族,就不难理解这样的不平等。
比方说,别人的父辈甚至祖辈就通过“做题”早你一步、两步先到了大城市,所以别人的起点就比你高,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而现在的你,自己也通过做题留在了大城市,相比你那些还不得不留在农村和小城镇的亲戚朋友,你不是也给自己的下一代搭好了梯子,提高了你下一代的人生起点了吗?
这就是家族积累啊!
人的体力、智力、外貌、勤奋程度各有不同,总会有人比你先富起来。
你要是想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不允许别人先富起来,那么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必须留在贫穷的原地,止步不前。
只要这些不平等不是因为权利不平等造成,而是由于能力或勤奋程度的差异造成,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人与人之间先天与后天的差异,要么是无法消除的客观现实,要么消除它是不符合私产伦理的。
但权力制造的差异则是可以通过削减权力来消除的,而且符合真正的公平正义。
也只有权力制造的不平等,才是真正值得也应该谴责的,解决办法是尽量减少权力和垄断,给市场松绑,给人们的自由松绑。
权力是封闭的,它本身就是一道墙,一道阻止人们自由创造财富、自由追求幸福的墙。
而编制就相当于在墙上开了一扇窄窄的门,这扇门被权力把守着,它选中的幸运儿可以穿过这扇窄窄的门,到达一个幸福稳定的天堂。
人们总是在抱怨这扇门太窄,抱怨权力对他们不公平(主要是没让他们通过这扇门)。
他们时常议论这道墙该怎么砌、门应该开多大、能不能多开一扇门,旁边的土奥看不下去了:你TMD就不能把墙拆了?
2022-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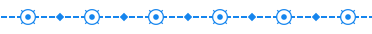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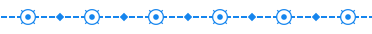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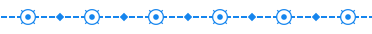
张是之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这次他做的精读训练营,精读的是奥地利学派经典著作,米塞斯写的《人的行动》(也有翻译《人的行为》)。
这本书很值得精读,但也有不小的难度。当年我先读了《真实的人的经济学》等几本奥派入门书,然后才开始读《人的行动》,可还是觉得很烧脑。
张老师这个训练营可以帮助你学透这本书,非常值得加入。他带着你花一年时间精读,不是那种 30 分钟带你读完一本的快餐。
发送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