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成这样,还不如去死
努力日更中
我家姑娘去上学了,准确说,是去做题了。
所以,今天聊聊“做题家”这个话题。
做题家,有时候又被饶有意味地说成“小镇做题家”——好像大城市里的做题SB不多似的。
舆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掀起一波对“做题家”的嘲讽。“做题家”这个说法似乎是要批判所谓的应试教育。
但根据我的观察,嘲讽做题家或批判应试教育的主力,大概有这么几类人:
1,无法忍受家长和/或学校强制教育的人。
2,在应试教育规则下尝试过努力,但是不够成功的人。
3,自愿适应应试教育规则,并获得过成功,但是在现实中生活得不如意的人。
(以上归类和判断都是经验归纳,肯定不完全。例如,如果你认为自己又是做题家出身,又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好,又对强制教育不满,自然不在以上归纳之内,不必着急对号入座。)
第一类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的确在家庭和学校中,对学生的强制规训普遍存在。严格说,这种反感其实是对强制本身的反感。
而这种强制规训之所以广泛存在,恰恰是因为制度性的强制存在——那就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英文是:compulsory education,它就是“强制教育”的意思)和公立学校体系。
它的强制性不仅仅体现在“义务”和“公立”上,还有整个高等教育的计划经济模式——统一考试、按分数和指标入学。
供给方和入学方的自由选择权都非常有限,所以即使存在名义上的民办中小学和民办大学,家长和学生教育可选项也非常少,只有存在不同的教育供给和不同入学要求的大学,才可能让中小学教育内容和方式多元化。
所以,大部分家庭和学生只能选择现有的垄断与计划性的教育服务。非常讽刺的是,这种教育体系恰恰得到了许多普通人的支持。
很显然,反感应试教育与赞成义务教育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本文不展开来谈。
有必要着意指出的是,上述第二、第三类人反对应试教育,往往不是出于要求自由与权利,而是出于loser心态。
第二类人往往是这样的:我本来是认同高考的,但最后我发现我考不过别人,所以我就攻击比成绩我好的人是做题家,贬低他们的价值。
这种鸡贼和无赖,不仅家长和学生中存在,教师中也大量存在。有许多对应试教育唱反调,写文章获名获利的老师,就是这种在应试体制下教学业绩差劲的人。
第三类人比第二类人更加鸡贼和无赖,在做题成功阶段,他们几乎不会真正抱怨和反抗,相反,他们会享受自己成功的喜悦,享受来自同学、老师、家长和亲友的赞美,也骄傲地享受很好的高等教育。
他们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是自己比别人更加优秀更有能力或者付出更多的结果,一切都理所当然。
但是,当他们发现在大学里,评价体系更加多元,竞争更加激烈,对自我选择和自律要求更高(因为没了从前的那种变态高压),并因此而无法获得过去那样的成功时,他们开始抱怨一切,除了他们自己。
无论是哪一种论调——只要能够支持他们的抱怨,都迫不及待拿过来用。
当他们发现要走向社会时,社会的选择机制多种多样,他过去以做题碾压过的各类人都可能获得比自己更好的机会,更好的生活时,他们开始喷射愤怒和仇恨。
他们的一切心理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只要我过得不如意,那么全世界都欠我的。
内卷这个词从去年到今年的泛滥,最早就发端于高校师生——一群享受着税金供给特权的巨婴。
为了生活,他们可能忍气吞声,但满心的不甘、嫉妒、仇恨,配上合适的说辞——各种煽动民间斗争与仇恨的所谓社会学说,尤其以我们中学课本的观念底子为代表——足以使他们忘记自己的无能和不自律,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可能狰狞地爆发。
而更“聪明”更有策略的那些人则是,利用自己的做题优势,逃避市场竞争,继续呆在垄断的、被税金豢养的公共学术体制内,炮制类似的说辞,煽动民间内斗和内乱,借助观念的力量,来消灭自己臆想中的对手,从而进一步保住自己的优势和特权。
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成功或者不成功的做题家。我们不得不在郭嘉教育体系内上学。要怎么才能避免成为第二、三类人呢?
理解最日常、最诚实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自食其力的,以市场为生[打工也是市场方式]的父母亲朋的生活方式),从中领悟亘古不变的常识:
人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负责。人应该从与他人的合作与自愿交换中获得幸福(致富,或者其他益处)。
其他偏离这些轨道的观念,不管它来自哪里,不管它多么动听,都要保持警惕。
我们上学是为了未来生活可能有更好的生活。
比如说,基于生活经验,考大学可能是我们认知中的当前较优可选项,那么我们可以去努力追求分数。
但是更要知道,分数并不等于真知,在社会科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等——领域,教科书更不等于真知。
上学的年轻人(高中生和大学生),至少有一个普遍的优点,那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理想主义——它的含义是,愿意以某种观念来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有价值的。这是一种珍贵的品质。
然而,它易碎、易变质也容易走向反面。
在没有走入社会之前,它的变质最容易发生在这一点上:即认为,我看不惯的生活就是丑陋的、鄙俗的、应该被消灭的。
这样,它就演变成“非我族类,必欲诛之”的凶残观念了。
要使理想主义在思想上不那么变质,最重要的不是情怀和信仰,而是保持理性,用逻辑一致去检验自己和他人的言行,保持理智的诚实,有错即改。
理想主义这个词就是idealism,在英文中,idea本身就有思想、观念的含义,而思想、观念本身又是人的自觉意识——即理性的产物。
理想的内容本身可以改变(因为我们可能错了),但理性和逻辑是我们检验理想的唯一工具——即使增加更多生活经验,也仍然需要我们运用理性去理解和分析经验,并纳入到观念的整合中去。
当我们思考中发现困惑时,无非是知识不够或者推理错误。
无论多么动听的言辞,都要尝试去抓住它的因果链,如果发现了矛盾,就决不放弃质疑,决不不假思索地将好听的,符合我们某种情感直觉的或被默认为共识的观点当成真理和生活的信念。
如果实在困惑太多,可以再次回到常识原点: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自我决定、自愿合作与交换,以及用可行的策略反对、反抗或消解一切施加到自己身上的暴力强制。
用这些框架合逻辑地,也合生活经验地整纳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至少不太容易走上过火的邪路。
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开始仇视生产者、仇视自由竞争者、仇视自己看不惯的普通人;
发现自己开始把不事生产却鼓吹仇恨外人和征服的战争狂、坐食税金却鼓吹管制民间的ZZ人物、被税金豢养却认为民众应该听他们教训的知识分子、用抽象的价值强制个人生活的各类神棍(包括民族主义分子、zz狂热分子、各类宗教狂徒等等)视为偶像;
开始认为诚实生活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被我们认为眼界狭窄和过时的父母和同类的生活常识和日常道德都一文不值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成为普通人的祸害了。
读书读成这样,还不如去si。
另外,我当然也知道,那些在现实中诚实生活、辛苦劳作的人们中也有许多类似的错误观念。
批评多数人的某些观念,容易遭致直接的反感。这是真话和实话的宿命。
但我不担心。因为我自己就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
我不仇恨自己的出身和阶层,不鄙视自己的同类,而且我也清楚并且承认,在这些观念讨论之外,我自己的一切生活来源都离不开于与普通人的互动——如果不与普通人合作与交换,我寸步难行,难以为生。
我所说的一切,也都是希望普通人活得更好——更富有、更幸福。不甘、嫉妒和仇恨只会让我们更加不幸,看清楚真正的侵犯、掠夺和剥削来自哪里,也更能使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减少损失和痛苦。
多数人可能(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把批评者挂在路灯上,批评者也可能害怕挂路灯而闭嘴,但是,痛苦和灾难不会因为消灭了批评者或让批评者闭嘴而自动消失。
如果是这样,那么受伤害最深的,也一定会是这普通的多数人;最助纣为虐的,也一定是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要么拿着笔,要么拿着枪。
文/可二
2020.12.17
课程内容:《经济学入门50讲》视频精读
主讲人:作者张是之
课程形式:视频(PPT+字幕)
课程难度:入门级,经济学科普级
适合人群:对经济学感兴趣,虽然读过《经济学入门 50 讲》,但自己看书还是有一定难度朋友;或者部分内容没有理解,想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朋友。
完成情况:目前已完成录制 12 讲内容,后续陆续更新。
更新频率:计划两个月内完成所有 30 讲内容的视频讲解。(书上后 20 讲内容相对简单易懂,完全理解前面 30 讲,后面 20 讲完全没有问题)
课程售价:最终价格 99 元;目前价格 49 元,越往后越高。
超级会员可再享受八折优惠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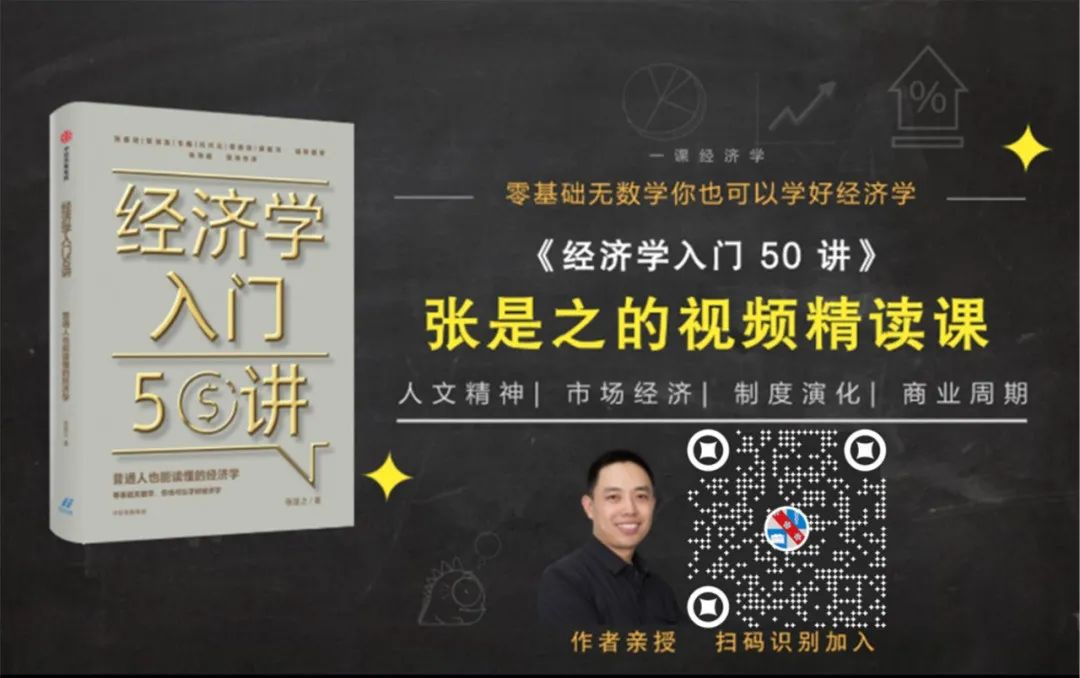




发送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