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了,躺平了,全世界都清净了——本号停更原创,坐等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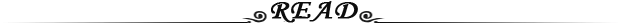
早两天,老古的两个公众号被封,我非常生气。
我这样的庸碌成年人,生气能干什么呢?
有一篇古文《唐雎不辱使命》说,“庸夫之怒,以头抢地尔。”就是说啥也干不了,只能自残。
庸夫的自残,其实是夹杂了害怕。
所谓兔死狐悲,我很快想到,自己的号可能也快不保了。
最近连载的《米莱时代》,其实快收尾了,但我的校对和注释工作还差一点点。
过两天接着发。
译文的阅读量向来不高,但连载一个月来,这个系列的阅读量在节节攀升,最高的一篇《一个惊天秘密,米莱已经告诉阿根廷人了,但中国人还不知道》已经到了7万,还有几篇接近破万。
如果在一个正常社会,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在这里不一样。我po的内容,虽然鲜涉时政,都是准学术类文章,但阅读量越高,号越不安全。
每次文章破圈,都有大量谩骂、低智以及恐吓的留言、私信涌进来。
米莱提到,在过去,阿根廷人羞于公开表明自己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我们这里也庶几近之。认同者不敢表态,不认同者毫无宽容与尊重之风。
在此种风气之下,牠们顺水推舟,灭了你,也是意料中事。
所以,又气又怕中,我决定:
1.调整本号定位,不再发自己写的原创内容。
2.备份所有文章,以防被夹。
3.开设一个备用号“可二自留地”(见文末),收容本号读者,此号将主要发布古老板过去正常发布的,以及已经通过出版社审核,准备结集的文章。
这个事情本来昨天就要做,但是朋友邀我到海边来玩,就拖到了今天。
海风一吹,完全不生气,也不害怕了。
江渚渔樵上,一切皆笑谈。
最后掉个书袋,解释一下为什么改成“奥派同文馆”。
除了自欺欺人地免去个人痕迹,用这个名称,是有出处的。
“同文”二字,首见秦朝,暴秦大一统措施中,有“书同文”之举,取“统一文字语言”之意。
其旨不可谓无可取之处,但以国家权力/暴力强制推行,与许多同类举措一样,正应了西方的一句谚语:凡通往地狱之路,皆以向往天堂的善意铺就。
秦朝的暴亡,就是过度依赖这类举措的结果。
北宋时,已设有“同文馆”,是接待吐蕃、高丽使臣的对外机构。
今人所熟知的“同文馆”,来自晚清。
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甫停,清廷内部掀起洋务自新运动。
1862年,恭亲王奕欣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明确其宗旨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光绪年间,清廷官员许銮曾作过更加详细的解释:“中外文字不同,通商往来,文移必资通晓。因设此馆,选少年送入,并习外洋文字。名曰:同文。”
可见,此时的同文馆,主要是翻译人才培养机构。
其英文译名更加明确:在官方档案中,同文馆前期的英译名是“Interpreters College(译员学院)”。
本号最近以译文为主,今后也不打算发原创文章,“同文馆”这个名称非常贴切。
当然,无论是洋务自新的“同文馆”,还是我等用爱发电的自由市场主题译文,都不是纯粹的功能性翻译。
晚清同文馆聘请的总教习是洋人,其中有一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丁韪良(W. A. P. Martin),他把“同文馆”重新译为“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共同学习的学校)”,并且自1867年起,在同文馆内增设算学、天文、国际法等西学课程,意在培养复合型人才。
我们的翻译,也是为了介绍西方近现代,乃至当代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变革、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核心经验。
这自然也是一种共同学习。
相信有心的朋友,也会经由这些译文,去探索更广阔的新知,或者发掘被人遗忘的真知,温故知新,鉴往知来。
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同文馆”之名,同样十分贴切。
然而同文馆,还另有一番典故。
北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新皇哲宗推翻祖母垂帘时期的“旧法”,重启王安石新法。
新党领袖章惇、蔡京(就是《水浒》中的蔡太师)掌权,他们大兴政治迫害,打击不同意见者。
前宰相刘挚等一大批被迫害的知识分子被囚禁的地方,就是上文提到的北宋同文馆。
此时北宋政治黑暗,边防虚弱,王安石的“凯恩斯主义”变法又把经济搞残了,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正经的对外交往。
涉外的同文馆废弛已久,正好拿来做监狱,关押不同意见者。
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本号改名于言路受制时刻,也与同文馆的这一渊源遥相呼应。
是为记。
另,正打算发布本文时,看到古老板又开了一个新号,公号的介绍是老古的最后一勃/搏,欢迎各位关注:
本号备用号: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