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越热,心越热——世道不好,越要搞事





有人跟我说,你讲错了吧,应该是天越热,心越凉。
你看看这世道。
所以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不过,有时凉热也可以同体。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纳粹甚嚣尘上,米塞斯在维也纳跟朋友们打笑,说,
未来可能要去南美了,我可以在那里做门童,我当过兵,站姿好。
笑声背后,是这个狂热世道给他带来的彻骨凉意。
然而,他终究没有去南美冷眼避世,打发余生,
而是转头去了同样讲德语的中立国瑞士,在那里写下了一本书《国民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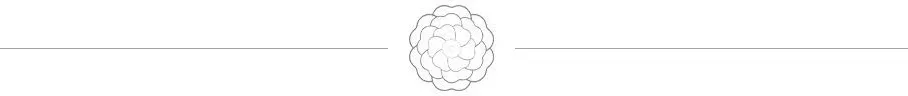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1941年,米塞斯流亡美国,寻大学有薪教职无果,生活拮据。
但仍不愿曲学阿世,不向罗斯福新政及其知识祭司——凯恩斯主义妥协,不向新政府献媚。
大约同一时期,他的半个学生,早已在英美学界立足的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在安全的美国对着苏联和纳粹法西斯一通猛烈输出。
米塞斯则写下了《全能政府》(1944年)。
与哈耶克不同,他左手批纳粹和苏联,右手批英美,说二战的根源是全球盛行的国家控制主义和干预主义。
直指民主世界对战争也负有极大的责任。
接着又抖擞精神,将《国民经济学》改写成煌煌巨著《人的行动》,成为奥地利学派的集大成经典著作。
它没有主流经济学明里暗里对权力的谄媚。
也没有后者那种晦涩佶屈,似乎可任意解释的象牙塔流弊。
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整套观察和认识世界的工具。
所以,它不仅仅是经济学,而是大社会学(Grand Sociology)。
借助这套工具,它清晰一致地理解和分析人与社会,系统地审视和批判着社会、经济与政策方面的各类愚蠢与错误。
凭着这些努力,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在美国重建了奥地利学派传统,惠及后世,一至于今。
可见,刺骨的凉意从来没有浇灭米塞斯的热情,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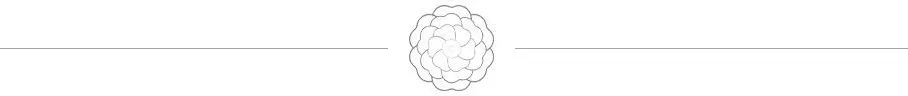
这个夏天,有一个人大概也想做一点类似的事。
萤火自不能与日月争辉,但在暗夜中亮出一点微光的心志是一样的。
掐指一算,用经济术语来说,我们现在处于商业周期的萧条期。
物价下跌、投资低迷、失业增加。天气很热,人心很凉。
他说,要不,正好,我们来读一点经济学吧。
就读八十年前老班长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他喜欢按不对习惯,见到老兵就叫班长。
无论是衰世避祸自处,还是盛世趁势进取,都需要系统的分析视角和工具。
他说,要看清这个世道的迷眼乱花,了解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静心读一读米塞斯,会大有裨益。
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各经济部门都在清算和调整,暂时的困难,是未来起飞的前奏。
具体的个人也需要停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如果被形势逼停,更需要学习和思考。也只有这种时候,才是最好的内省时机。
越是这种紧要时刻,越是心要静,脑要灵,但血不能凉,斗志不能熄。
要不然,繁荣期一来,有机会搞钱时,又容易手足无措。
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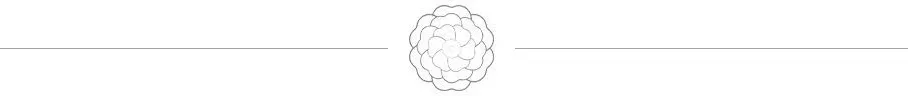
那怎么读呢?
他说,可以有很多姿势,站着读,坐着读,走着读,找牛逼人的带读,还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夫人(老公)或别人的夫人(老公)一起读。
这个人哪,名叫张是之,这些年陆陆续续出了什么《经济学入门五十讲》,《米塞斯行动学100讲》之类的书。
还搞翻译,出了本美国当代大帅哥奥派学者裴德荣的译著《如何思考经济?》。
还在《南方周末》开什么经济学专栏,我也不懂是不是专栏,反正左一篇右一篇,隔三岔五地见报。
还开了一个公众号,名字就叫《奥派经济学》。像条不知疲倦的黄牛一样,勤耕(更)苦干好些年了。
总之,比许三多还能整活。
冬寒夏暑都坐得住,做人做事都很靠谱。
一句话,耐得烦,信得过。
他的暑期读书方案点击可见:《读书不必万卷,行路不必万里》。
不过,他跟我说这个设想时,我立刻怼道,理是这个理,但这个鬼时候让人费力费米跟你读这些,你是不是疯了?
这个货本来就很疯。
没有一点神经病,谁会干他这些年做的这些事啊。
吃力不讨好,左右难逢源。
但正如我的朋友古原所说,这个世界就应该对生产者(企业家、商品和服务供应者)残酷一些。
所以我一点都不心疼他。
我跟他说,来,你想做这个事,先让我砍一刀。
他说,好。
我不客气地一刀剁下去。
他咬牙死挺,说,痛,但死不了。
到底怎么砍的,结果如何?
他不让我公开说。
剧透一点点:砍出了一个让搞事的人欲哭无泪,让凑事的人不好拒绝的价格。
更详细的情况,各位加我的微信woodcloudyyy问一下我就知道了。
小柯基,原昵称可二,出生于阿卡林,啥也不是,一个假装书呆子的二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