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自由金本位沦落到纸币本位,一百年来,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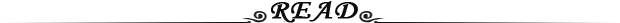

在本文中,我将延续米塞斯、罗斯巴德和萨勒诺的传统,探讨健全货币制度对货币质量的影响。
货币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类似,取决于使用者对其效用或品质的认可。
货币质量可以定义为“行动人感知到的货币履行其主要职能——即充当交换媒介、财富储藏手段和记账单位——的能力”(巴格斯,2009年,第22-23页)。
货币质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其购买力。而货币制度的质量,则是指一种货币体系成为优质交换媒介、财富储藏手段和记账单位所提供的制度框架的能力。
尽管货币体系或制度的质量是由行动人主观感知的,但存在若干客观特征往往会左右这种感知。
在试错过程中,行动人通常不会将对制度框架的认知建立在反复无常的臆想之上,因为误判的后果将由他们承担。
在货币体系客观特质的引导下,参与者往往能通过对冲贬值风险或从货币升值中获益,从而更有效地守护其货币财富。
本文将对"优质"货币体系的这些客观特质进行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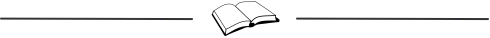
我将分析不同属性的部准金本位制度。当然,我不会穷尽所有的理论可能性,而是集中探讨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货币制度。
首先,第一种部准金本位制是金币本位制。在该体系下,银行持有部分准备金,同时金币参与流通。
就交换媒介功能而言,金币本位制与100%金本位制具有相似特性:黄金不会腐坏、质地均匀且单位体积价值高。
然而,关于货币质量的主要差异,在于其作为财富储存手段的功能。
在金币本位制下,比起百分之百金本位制,政府更容易操控货币,因为政府通常垄断铸币权。
此外,银行被允许发行信用媒介,即不以黄金背书的货币替代品。银行体系不必持有百分之百的储备金,因此信贷扩张成为可能。
信贷扩张通过引发商业周期削弱经济,并有助于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在经济衰退时,存在政府救助稀释货币价值的风险。
衰退也可能被用作增加政府经济立足点的借口,例如设立中央银行。
如果设立中央银行,货币质量会进一步下降,因为该机构是政府进入货币体系的立足点,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货币质量。
此外,信贷扩张还扮演了期限错配的助推角色,即“短借长贷”。
当短期债务面临展期问题时,银行可能会动用自有存款作为替代性融资手段。同时,信贷扩张通常会增大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期限错配的风险。
然而,过度的期限错配趋势将导致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进而更易引发政府救助——而政府救助往往伴随着货币本位的恶化。
此外,部准金本位制与百分百金本位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货币数量增加对其质量的影响。
在百分百金本位制下,新开采的黄金无疑与原有货币具有同等质量,货币品质不会下降。
然而在部准金本位制中,当信用媒介(即纸币)数量增加时,由于每单位货币对应的黄金储备减少,货币质量随之下降。
准备金比率收缩,货币的平均担保水平也随之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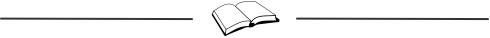
金块本位制往往从金币本位制演变而来。
在金币本位制下,信贷扩张会引发周期性银行危机,银行机构往往施压要求建立最后贷款人机制——即中央银行。
与此同时,银行希望减少流通中的铸币数量,这一诉求在金块本位制下得以实现,因为政府不再铸造金币。
通常情况下,黄金储备会集中存放于中央银行。
货币以金块作为支撑,储备金集中托管于中央银行。
货币可按固定汇率兑换为金块。金币很可能从此退出流通领域。
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中,相较于金币本位制,货币质量会出现下降。
由于只有金块才能兑换货币,民间囤积黄金变得更为困难。
受制于金块兑付和运输的困难,货币兑换黄金的需求将减少,黄金实际上会退出日常流通领域。
这使得银行能够降低黄金储备规模,从而为信贷扩张创造更大空间——这种扩张通过商业周期削弱经济活力,并为政府债务货币化提供便利。
当银行持续削减储备时,其流动性状况会日趋恶化。
虽然更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与中央银行的设立能降低期限错配风险,但过度的期限错配依然会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随着政府救助概率上升以及货币制度的持续贬损,货币质量将不断恶化。
由于公众持有的黄金数量较少,政府更容易全面暂停兑换,而无需实行双本位,也不会面临民众拒绝上交黄金的阻力。
这样一来,政府就能更轻松地操纵货币,使货币本位逐步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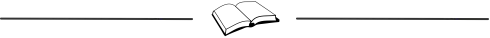
货币本位质量的进一步下降体现为金汇兑本位制。
金汇兑本位制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这一制度下,各种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一种主导货币挂钩,而这种主导货币可以兑换为金块。
只有中央银行才能通过主导央行将一种货币兑换成金块,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运作便是典型例证。
金汇兑本位制导致黄金储备进一步集中化,并允许主导国家以外的银行体系在该主导货币基础上扩张信贷。
主导银行体系同样可能利用其特权地位来扩张信贷。
若主导国家持续扩张信贷,则该体系将播下自我覆亡的种子,从而将代价转嫁给其他国家。
这种特权地位的滥用终将遭遇其他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纷纷开始要求兑付,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法国政府要求用黄金支付时所发生的情形。
由于信贷扩张能力增强,商业周期的波动将变得更加剧烈,从而损害经济。
此外,债务货币化在更大规模上成为可能。期限错配加剧导致金融体系更趋不稳定,从而提高了稀释纾困资金的可能性。
物价通胀趋势亦随之加剧,这反过来刺激人们承担更多债务。
民众与黄金的日常联系逐渐松散,当政府彻底切断这种联系时,遭遇的阻力也将更小。
需要指出的是,在金汇兑本位制下成为主要货币,从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提升该主导货币的质量。
担任国际储备中央银行具有极高盈利性(Rittershausen 1962年,第408页)。其他中央银行必须以极低利率持有主导货币储备。其他央行必须警惕贬值风险,贬值将导致其资产缩水。
因此,当一种货币成为主导货币时,就意味着其质量得到了提升。其他经济主体更有可能接受并持有该货币。
在这些部分准备金制度中,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体系:一种是记账单位与交易媒介相互分离的体系,另一种是合二为一的体系。
在记账单位与交易媒介分离的体系中,人们以黄金等货币进行核算,但同时也使用银行券或存款等其他交易媒介进行支付。这些银行券和存款相较于以铸币支付可能存在贴现。
因此,信贷扩张可能导致贴现率上升,但不会损害黄金货币的完整性——以银行券计价的物价会上涨,而以铸币计价的物价则不会。
反之,若因法定货币法要求银行券和存款必须按面值兑付,该体系的质量就会下降。
这种情况下,信贷扩张不再表现为贴水,但会因以黄金计价的物价上涨而降低铸币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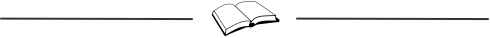
当货币制度最终彻底停止兑现,法定纸币随之出现时,货币体系的质量将发生急剧变化。
自1971年起,全球正式迈入法定纸币本位时代——在这一体系下,即便是中央银行也无法将货币兑换成金块。
货币不再具备兑换特定数量黄金的任何保障。因此,货币的质量已然下降。
如前文所讨论的金本位制下可兑换黄金的债权,与不可兑换的纸币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不可兑换纸币所代表的债权指向未明确指定的标的物。法定纸币的价值会随持有者对其购买力的预期而波动,这种估值可能急剧下跌甚至归零。
其价值完全依赖信任维系——若信任崩塌,即便货币数量未发生剧烈变化,其价值也可能迅速跌至零点。
不可兑换纸币作为财富储存手段的能力,完全受制于其内在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可兑换的货币凭证则不会出现此类问题——例如,随时可兑换黄金的银行券。
正如里斯特(1966年,第200页)所总结的:“简言之,可兑换性不仅是限制数量的手段;它还赋予了银行券法定性质和经济特质,这些特质是纯粹纸币所不具备的,且与数量多寡无关。”
因此,在金本位制下,当银行券和存款的兑付被暂停时,货币质量将迅速恶化(这与货币数量的变化无关)。
一旦暂停兑换,货币价值便失去了可依托的安全底线。
货币不再与黄金的工业需求产生关联,而“黄金的旺盛工业需求为货币持有者提供的‘保障’”也随之消失。
新纸币的生产成本极低,这加剧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兑换暂停,针对政府操纵货币的最后一道防线已不复存在。政府操控货币供应的闸门已然敞开。
如今对政府的唯一限制,就是其自身对增发货币设限的意愿。这些限制通常通过中央银行的法规和授权正式确立。
由于中央银行具备无限印钞并救助银行的能力,道德风险随之滋生。
期限错配现象愈发严重,准备金比率持续下滑。
信贷扩张使得商业周期波动更为剧烈,对经济造成显著损害。通过印钞机实现政府债务货币化的操作变得愈发便捷。
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较以往加剧,政府救助的可能性不断上升,同时货币质量持续恶化。
其结果是,货币实际上丧失了作为可靠财富储存手段的功能。价格通胀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
当人们逐渐适应物价上涨后,便开始承担更多债务,导致经济体的负债水平和脆弱性双双攀升。
因此,在货币体系退化为法定纸币体系之际,货币质量将急剧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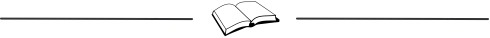
货币质量的变化既可以在特定货币制度框架内发生,也可以通过改变货币制度来实现。
沿着上文所述的“质量阶梯”从下往上移动——即从法定纸币制度,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金块本位制,接着到金币本位制,最终到百分百自由金本位制——任何一步都意味着货币质量的显著提升。
反之,沿阶梯下行则预示货币质量恶化,并引发通货膨胀倾向。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制度的降级更为常见。特别是在备战或战争期间,货币制度往往朝着劣质化方向演变(里特斯豪森1962年著作第366页)。
历史上曾出现过货币制度改善的情况。
例如,恢复铸币支付(即从法定纸币制度转向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发生过,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暂停铸币支付后,后续往往会恢复这一制度。
典型案例包括拿破仑战争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恢复铸币支付,以及1879年美国内战后恢复铸币支付。
当人们预期将恢复铸币支付时,会预判货币质量提升,货币价格可能会立即上涨。这或许是1879年美国恢复铸币支付前出现价格通缩的原因之一(Bagus 2015)。
另一例证是1844年颁布的《皮尔银行法案》,该法案禁止发行无担保银行券。该法案的缺陷在于未将银行存款纳入条款。若当时对活期存款也实施100%准备金率要求,本可显著提升货币制度的质量。
然而总体而言,货币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从高质量金本位制向低质量金本位制退化,最终演变为法定货币标准的下降趋势。
事实上,一旦我们放弃百分百金本位制,货币体系逐步恶化的种子便已埋下。政府由此在货币体系中获得立足点。中央银行的信贷扩张会导致严重的期限错配、债务过度累积和金融体系不稳定。
在这些货币制度引发的危机中,救助行动往往接踵而至,这会推高政府债务,而这些债务随后又会被货币化。
在这类危机中,现行货币制度也常常遭到破坏。例如,在银行业危机中,铸币兑付可能会被暂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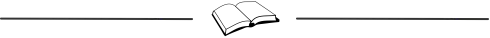
除了货币的数量外,其质量同样会对购买力产生影响。
本文深入分析了货币制度的质量,这种质量主要体现在为货币作为良好交易媒介、价值储存和记账单位提供稳固的制度框架。
货币制度的变革可能导致货币质量发生实质性变化,进而影响货币需求和购买力。
在众多货币制度中,最高质量的当属百分百金本位制。
然而,部分准备金本位制却潜藏着自我恶化的风险,通过信贷扩张可能引发经济和银行业危机。
随着政府干预的逐步增强以及准备金集中化的推进,金币本位制将逐渐退化至金块本位制,最终演变为金汇兑本位制。
从金汇兑本位制转向法定纸币本位,标志着货币体系的重大转折。
货币单位不再具备非货币需求的支撑,其价值完全依赖于公众的信任和信心,而原有的充足非货币需求保障已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下,政府和中央银行对货币事务的掌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金融体系的周期性衰退与纾困措施逐渐常态化,导致货币质量持续下滑。
未来的研究或许应更多聚焦于不同货币制度的质量差异,以及制度转换对货币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在经济衰退时期,转向更高质量的货币制度,可能对提振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


连载合集



推文精选
